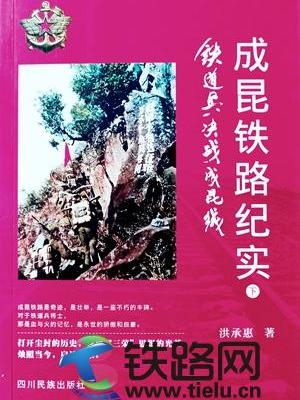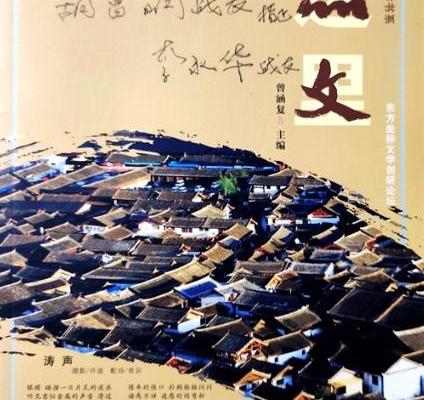我的书房有个雅号:映雪堂。之所以给书房起了这样的名字,是源于一位同姓祖先的故事。这位祖先是晋朝人,名孙康,小时候喜欢读书,但家境贫寒,买不起油灯。冬天下大雪了,他发现书上的字在雪地里能看清楚,就借着雪光的反射躺在雪地里读书。最后,这个祖先官拜御史大夫,终有了大名。
这个故事是小时候父亲给我讲的。那时,记得老家的堂屋上还挂着一副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也是为了激励我用功读书吧,父亲还常常对我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些记忆在我的脑海中是根深蒂固的。
我的书房虽以“堂”而称,其实只是一间18平方米的“蜗居”。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是孩子上学时用过的。靠墙的一圈书柜,也跟随我搬过几次家了。每次搬家的时候,别的东西可以丢弃一些,唯独书是一本也不能落的。
那环墙而列的6个书柜,有3个柜子里是我年轻时读过的书,主要是哲学方面的,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唯物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课本,中外哲学史、文化史、科技史、宗教史,还有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黑格尔、卢梭、萨特、尼采的书,还有孔子、孟子、墨子、鬼谷子,以及张载、王阳明、康有为、梁启超、冯友兰、艾思奇的书。那些书是我攻读哲学专业的时候,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读过的。那些人类知识的总和总汇总集,曾让我在浩瀚无际的海洋中,有一种沉醉其中不能自拔的感觉。我深深感到了自己的渺校但正如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在那种海阔天空的深邃中,我还是奋力划着求索的双桨。哲学是一种反思的反思,是悬在半空中的抽象之抽象。在那些大哲们的思想轨迹和理论体系中,我努力培植着自己的逻辑思维,也不断升华着自己观察世界的宏观视角。
还有三架书是历史和文学方面的。有人类史、欧洲史、中国史以及文学史、散文史,还有那些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当然,也有鲁迅、茅盾、老舍、冰心、孙犁、柳青、赵树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现当代著名作家的著作。历史是看透世道人心的一面镜子,文学是形象化反映客观现实、表现心灵世界的艺术。那些伟大的作家用独特的语言艺术构筑的独特的心灵世界,让我深深感到他们是一个民族心灵世界的英雄。文学是神圣的。一个作家唯有受命于天根植于地,唯有具备深刻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才有写出传世经典作品的可能。无根的、肤浅的、没有阅读积累的写作,都只会是过眼烟云。
那些书柜都有双层抽屉,里面堆放着我几十年的日记。在那些纸张已经泛黄的塑料本本中,有蓝墨水、红墨水、黑墨水,有些字迹已洇染得模糊不清了。但那就是历史。记得莫伸曾对我说过,他在秦岭山区插队和在铁路上做装卸工的时候,生活苦呀,他就把那些苦涩的日子记录下来,他的文学之路就是踩着那些日记本一步步走过来的。我的那些日记也是我50年人生的真实存在。那些尘封的日记里有我一路经历的风雨,也有我的心理、情绪和心灵的秘笈。我常常把那些抽屉看作是一座心庙。人性的善恶、生活的悲喜、命运的沉浮,一切过往都构成了人生长河中的美好风景。
我的书房窗户是朝北的,照不到阳光。但那凸出的大理石窗台宽大,空在那里似乎有些尴尬,我就摆放了一些从这里那里捡来的石头和砖瓦。在追求金钱和豪华的当下,可能有人觉得这些东西灰突突的,又不是什么值钱文物,但我却视这些东西为宝物,那是我生命中曾经踏过的脚迎…
从宝鸡北首岭捡来的那个陶片,上面有仰韶文化的刻画和彩绘。我就想着,人类幼年的审美可能就是从那些陶片上闪射出了最初的光芒;从雍州秦公一号大墓中捡来的那块棺椁木屑,是秦人发明锯子的历史早于鲁人的印证。站在那些堆码如山的方直的大木前,我想到了那个百家争鸣和“牛人”辈出的黄金时代;从周原遗址捡来的那半块筒瓦,让我想象着周人3000年前营造的殿宇庙堂的规模,也让我想象着“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的那种如《诗经》里描述的土地的膏腴和生活的丰美……
我在那个叫陈仓的古城生活了13年,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是在那里度过的。一条渭河,南山北原。渭河两岸,还有神农祠、钓鱼台、五丈原、金台观、横渠书院……在那些历史人文厚重的地方,我看到了那些先前的巨人为这个世界立德立言立行的精神遗产,也看到了这个世界为他们树立镌刻的丰碑。他们的那种坚如磐石的人生信念、人生追求和人生故事,如春风夏雨一般滋养着我的青春成长,也给了我太多的生命感悟和前行的动力。
在那个照不到阳光的阳台上,还有我在“大荔人遗址”的洞穴中捧回来的一捧柴灰,装在一个小瓷瓶里。我知道那是刚刚直立起来的“智人”曾经使用过的烟火。那地方在洛河北岸的铁镰山下,离我的老家仅有十里远,那片土地也埋葬着我的祖先;还有我在华阴石碨乡的瓦渣梁上捡到的席纹、绳纹瓦片,上面写满了汉代京师粮仓曾经的繁华。那地方原来是渭河漕运的渡口,华阴老腔就是从那些纤夫的原始呼号中起根发苗的。我有幸在那个与我的老家同名的叫双泉的村子,与那些当红的老腔艺人有过一次关于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复兴的交谈……
在那个像小小的博物馆一样的阳台上,还摆放着老潼关西城门遗址上的一块青砖,还摆放着唐代黛祠楼旋转舞台上的几根金线,还摆放着从司马迁祠的“高山仰止”牌楼下捡回的几片落叶,还收藏着褚遂良《同州圣教序》的残缺拓片……
我的故乡在黄河、洛河、渭河三河汇流的地方。在那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我生活了16年。贾平凹曾经说,韩城合阳老朝邑一带,历史悠久,文化醇厚,道德刚健而文明,是国家的大德之域。我热爱我的故乡。我之所以要在我的书房摆放这些东西,是因为每当看到那些历史与现实的遗存,我就会想到渭北高原的农舍,关中大地的麦田,陇亩村头的亲近,天地山河的宏远。那些生之喜悦、逝之哀伤以及那种无尽的乡思和厚重的承载所凝结的情感,都像一个强大的磁场,牵引着我的脚步、我的思想、我的灵魂,也常常勾起我想要回报生我养我的故乡,写写那片土地的强烈的创作欲望……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如今,我从一个舞象之年的少年已变成一个天命之年的中年人了。当然,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我的阅读宽度和深度也在扩展。特别是随着社会接触面越来越广,我的许多杰出的朋友都有了自己的著作,每次聚会回来,我都是提着一摞子书。加之周末喜欢逛书店,我也喜欢去旧书摊淘一些旧书,如此一来,我的那间18平方米的书房就容纳不下那些接踵而来的“新朋老友”了。今年春天,我请工匠来丈量了客厅的长宽,又挨着两面墙订做了两排书柜。那些顶到天花板的新书柜,不仅放了林林总总的书籍,还放了我的那些奖牌、奖杯、奖章、绶带、证书。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文学照亮着我的生活,也改变着我的人生。
我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模样,我只知道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沉浸在如禅房一样的书房里,灯光如水流泻,书香如茶洋溢,或卧或坐或立,或读或思或写,兴起而作之,兴尽而止之,那是一种精神的自由、思想的激荡和游历的愉悦。春去秋来,寒来暑往,我就是这样幸福地生活在书房的春秋里。我以为我的那个叫映雪堂的小小的书房,无疑也是一片诗意的天空和斑斓的世界。
系西安铁路局机关干部)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