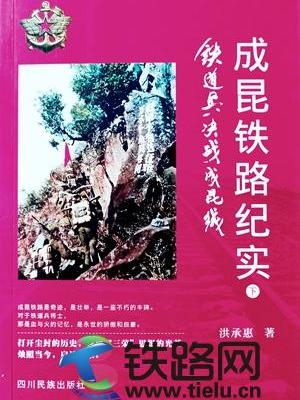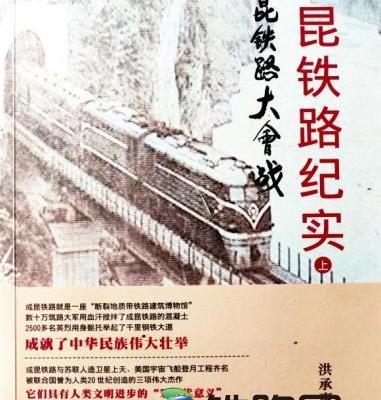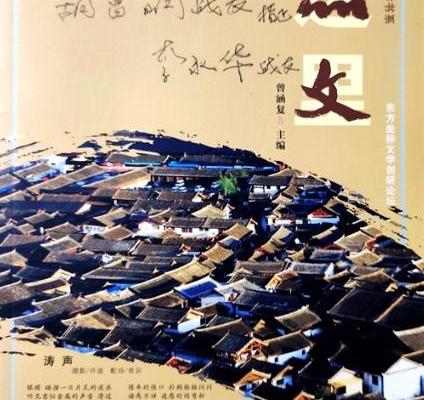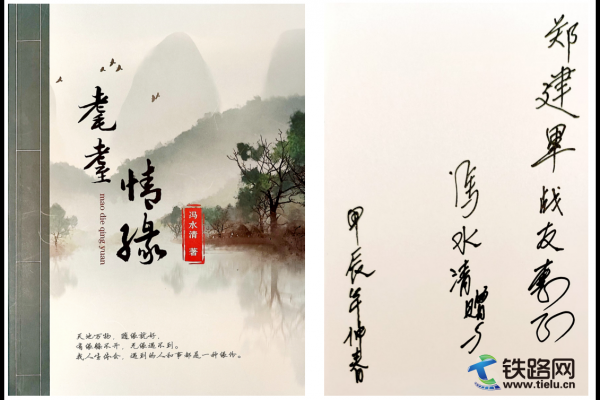林小静
2011年4月,我因一次偶然的机会,乘坐了大秦铁路的通勤车。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大秦铁路,但就是这一次,却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轨迹。
与许多人一样,在上火车之前,我对这条蜿蜒盘旋在燕山深处的铁路是陌生的。我甚至不知道它是我国第一条重载铁路,不知道它是一条煤运大通道,更不知道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用电与它密不可分。
那时候,我是一家公司的副经理,可以说,在大家眼里,我的这份工作相当不错。而我,也从没想过我会放弃现在的工作,从零开始,转行成为一名铁路系统报社采编人员。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当一名作家或语文老师是我的梦想,可是后来,读了土木工程专业的我,渐渐放弃了梦想,接受了现实,弃文从理。
改变,缘于那次大秦铁路之行,它又一次唤醒了我对写作的热爱。不,不能说是热爱。确切地说,是大秦铁路上的所见所闻,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内心和灵魂。
那次从大秦铁路回来之后,我在许多个夜深人静的晚上都难以入睡。我常常站在窗前,看马路上霓虹灯下车来车往,想起那群未曾见过面的养路工,心中无数次传出一个声音:走吧,到大秦铁路,去写写那群养路工。
4个月后,适逢太原铁道报社招聘采编人员,我看到通知后,决定报名参加应聘,因为我想走进那群养路工的精神世界。周围听说了此事的同事,都纷纷来劝我。有的说:这眼看着就要提级别了,你不等着提了?我说,不等了。有的说:你在房建部门会有更好的发展,现在走太可惜了。我说,不可惜。
我买了几本关于新闻写作的书籍,在工地上苦记硬背了一个多月,加上以前写作的底子,终于如愿考进了太原铁道报社,成为一名有机会进入大秦铁路采访的采编人员。不久,我通过试用,正式调入报社工作。从那时至今,我数次去过大秦铁路,去过这条铁路上最偏远的王家湾养路工区。而每一次,那里的养路工都会给我留下不同的感动和震撼。
我记得第一次去王家湾养路工区,是个初冬。我到达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正是吃晚饭的时候。伙食团窗口,15碗烩菜已经盛好,15名养路工正在端着稀饭,拿着馒头,准备吃饭。恰遇我的到来,大家立刻谦让起来,一人夹了两筷子咸菜,纷纷要把烩菜让给我。这时,工长李树仁命令大家坐下,一人一碗把烩菜吃掉。他说,晚上大伙儿还要到隧道里施工,不吃饱就没力气,没力气咋干活!说完,他悄悄把自己的那碗白菜炖粉条给了我。我没推辞,因为这时的推辞会被大家看成是一种矫情。我端起碗,拨出一半,和李树仁分了那碗烩菜。吃饭时,我看见一名叫布秉升的养路工,他端着半碗咸菜,低头在吃。我问他为什么不吃烩菜。他抬头看了我一下,然后盯着碗里的咸菜说,他喜欢吃咸菜。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想把自己的那碗烩菜,让给那些干重活的同事。据说,养路工们换钢轨、换石枕,肩上担的是四五百斤的重担。
在那个位于大山深处、蔬菜匮乏又交通不便的养路工区,一碗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烩菜,让我感动。
那一晚,我看到厨房里整齐排列的三大缸咸菜。我知道,那是这些养路工在大雪封山后,漫长冬季里的主要菜肴。
我还记得第二天,我临时决定要去常年在隧道里作业的河南寺工区,采访终年见不到太阳的养路工。我与工长王进,还有几名养路工经过王家湾乡的时候,王进让车停下来。他下车进了路边一个最大的小卖部,不一会儿,却空着手走了出来,在正午的太阳光下,一脸焦虑。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林老师,你到我们工区采访,我想买块肉,你不管咋的也是我们的客人,可这里买不到肉。我一听,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想,在城里生活的我们,买一块肉、吃一顿肉,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一件事。可对大秦铁路的养路工们来说,却是那么难的一件事。
城市的繁华与大秦铁路的艰苦,从那一刻起,一直像两个同样重量的砝码一样,在许多个白天和黑夜,撞击着我的内心。
两年多来,在完成采访任务的同时,我又多次去过大秦铁路。这期间,我遇到了在大秦铁路守了20多年的张文元。一心扑在工作中的他,没几年就要退休了。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家后好好陪陪家人,以弥补自己这么多年来对家人的亏欠。可他却被诊断为肝癌晚期,医院已经劝他放弃治疗。一心盼着与他团圆的妻子,千里迢迢从青海老家赶来,接他 “回了家”。虽然那次我和大伙儿为老张捐了路费,但他对工作的热爱和牵挂,却让我的内心无法平静。在王家湾养路工区,我遇到了老养路工占更江,他在大雪封山、缺粮断菜的寒冬腊月,为了让大伙儿吃上一顿蔬菜,独自走了10多公里的山路。在返回工区的时候,他连人带菜摔到了山坡下,冻僵在了雪地里。大家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省人事。在采访中,占更江从怀里掏出了一张20年前的全家福,用布满老茧的手指着照片上的一家人,幸福地对我说: “林老师您看,这是我老伴儿,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女儿。”他用手指给我看照片的时候,我看见他眼里含满了泪水。
那是一张黑白照片,听大伙儿说,每当月圆之夜,老占都会拿出这张照片,思念自己远在山东的家人。我还遇见了患尿毒症、做了肾移植的养路工祁志强,当我看到年纪轻轻的他,时不时就吞下一把药片时,不明真相的我,甚至反感过他的娇气。直到周围的养路工将祁志强的情况告诉我,尤其是当我得知祁志强在肾移植后一次次放弃上级让他回城的调令,坚守着深山中这一寸寸钢轨的安全后,我才如梦初醒,懊恼至极。也是在这里,我认识了在部队当兵时身体受伤致残的养路工刘海章。几年前,他听说大秦铁路需要人,便主动申请从家门口来到位于深山中的王家湾养路工区工作。我还认识了沿着父亲的足迹,接过父辈们肩上重担的新一代养路工韩建秦。如今,他已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成长为一名养路班长,与许多甘愿扎根大山、奉献大秦的年轻养路工一起,守护着这条煤运大通道。同时,我还从大家的口中得知了长眠在大秦铁路上的吴道普等人的事迹,大家带着我,去了他们的墓地。
我有一次去大秦铁路王家湾养路工区采访,住了数日,突然发起了高烧。于是,我被送上汽车出了山。在颠簸的山路上,发着高烧的我,一路上都在晕晕沉沉地想一个问题:如果这里的养路工生病了,他们会不会像我一样把工作暂时放下,出山治病?我想,他们不会。因为,那日夜川流不息的大秦铁路,离不开他们;而他们,也不会离开奉献了生命、倾注了心血的大秦铁路。
那次我被送到医院后,住了21天的医院。连同护士错扎的两针,我手背上共有23个针眼,但其中的16个针眼都扎在左手上,因为我想腾出右手来完成报告文学 《最可爱的人》的写作。
《一路二月兰》是我在大秦铁路采访时创作的一篇报告文学,许多通讯员和读者在看完后,特意在去大秦铁路出差之际,寻找过我笔下的二月兰。也有人打电话向我询问:我们怎么找不到二月兰?我说,一是你们错过了二月兰盛开的季节,二是二月兰其实是开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
我觉得,大秦铁路上的每一名养路工,都像二月兰那么纯净,他们甘于用平凡的身躯,点缀美丽的大地。
从第一次在大秦铁路的雪地里看到那些铁路前辈们的墓碑,到如今已经快3年了。3年来,我曾根据墓碑上的文字,一遍遍查找过那名叫吴道普的班长。当年,他在岩石风化严重的情况下,为了不影响施工进度,第一个扛起钻机走进了隧道。大塌方发生后,他被埋在了最里面。3年来,我一直都卡在吴道普墓碑上 “云南镇右”这个不存在的地名上,这让我对吴道普的身份和山脚下的那一座座坟墓产生过种种的猜测和假想。直到今年春节过后,当我再一次前往大秦铁路采访时,我才在他们的墓碑前,无意中从一个云南人的口中得知,吴道普的家乡在云南的镇雄。困惑我1000多个日夜的谜团,终于在那一刻真相大白。
那次从大秦铁路回来后,在我心中构思了两年多的 《静静的桑干河》终于动笔。半年来,许多个周末和夜晚,我坐在书桌前,用手中的笔,记录大秦铁路上养路工们的个人情感,书写他们心中的使命。每当此时,那一张张动人的面孔,都会浮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疾书不止。
人一生中,总有一些难忘的事,或难忘的人,而我最难忘的,就是扎根在大秦铁路上的那群养路工们。我想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在大秦铁路、在我国重载第一路、在燕山深处的桑干河畔,有一群可敬可爱的养路工。为了肩负的使命、为了国家的信任、为了人民的需要,他们心怀责任和梦想,为我们默默筑起了一座座精神的丰碑。
本版摄影 文国丰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