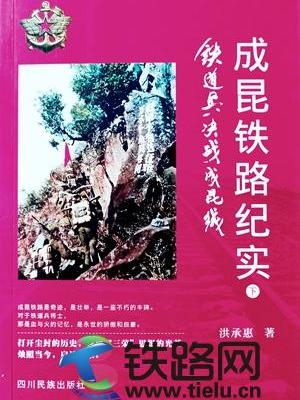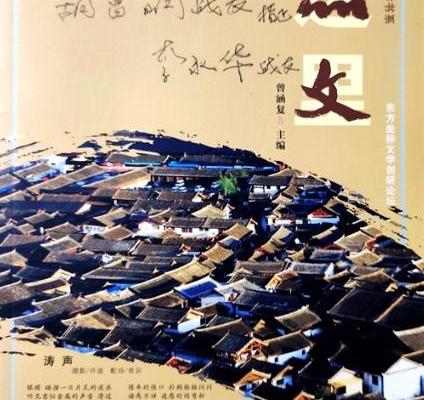我的小说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是因为截取的是我们生活的横断面,是人生的某个瞬间,不是传奇,不是惊心动魄的故事。我希望它是一缕清风,一束阳光,给人们带来的不是震撼,是触动,是抚慰和对人生的理解。
段。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铁路作协理事,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第十三届学员。发表作品100余万字,短篇小说《好日子长着呢》《亲爱的家》《正月》等被《小说选刊》选登。散文《照相》入选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中国企业职工文化大系——散文卷》。
最早读到黄丽荣的作品,是编辑《汽笛》专刊文学版她的散文,印象最深的是写铁路供电段那个《织毛衣的男人》。“我第一次看到他靠在座椅上,两只大胖手,捏着毛衣针,一针一针地穿梭时,我竟愣住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特别的人物和那种细腻的笔触一下子抓住了我。后来得知,她的所长在于小说。她共发表作品100余万字,短篇小说《好日子长着呢》《亲爱的家》《正月》等被《小说选刊》选登,深得编辑赞赏。
黄丽荣的小说有很强的画面感,像是夏天,满脸褶皱裹着小脚的外婆坐在一棵千年枣树下,摇着蒲扇给你讲故事。细细碎碎,絮絮叨叨。但仔细一咂摸,这生活的百般滋味都在里面了。画面背后,是一种贴近大地的深沉和穿越时空的深邃。采访得知,她的每一篇作品,其中每一个细节,都经过很长时间的打磨。本文旨在呈现一位铁路基层女作家耐心接受生活磨砺、细细与文字缠绵的历程。
<b>记者:很早之前铁路文学圈的朋友介绍您,都突出了“基层”这个关键词。据我所知,很多写作者会随着知名度提高调动到跟文字有关的岗位。20多年在铁路供电段的同一个岗位默默创作,您的这种坚守,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情怀?
黄丽荣 (以下简称黄):</b>在天空下,在铁道上,有一条能源之河,如织的高压线、高耸的电线杆、静谧的变电所,是这条 “电河”里的元素。诗人们称之为 “电流穿过诗行”,那就是我的工作:铁道供电。
1987年我从太原铁路机械学校毕业,一直就在京哈沿线的一个变电所工作。变电所是倒班制,两个人一班,我家住北京,上班要到河北,交通不便,所以上班下班都不容易,一来就是几天。最长一个班值了9天,把书啊、报纸啊都看了,没的可看,就盯着设备区看,心里很是烦闷。这时,电话声响起,是刘师傅,在离我几十公里处的小变电所值班,一个人看设备,每天他都给我们打个电话,汇报一下设备情况。这一天,他有些不舍,话有些多,他告诉我,明天下了班,就不来了,就退休了,他让我转告工友们,问候大家,他挺想大家伙的。一时间我愣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是安慰?是祝福?仿佛是我即将离开,我心里酸酸的。关于刘师傅,我有所了解,实在、勤勉、敬业,他是自己申请转岗过来的,原来在接触网干了二十几年的工长,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他情愿一个人,守着一份工作。一个人,比我们这里还要清苦,还要寂寞。
我放下电话,心绪久久不能平复。我倚在木门上,仰头,就看见了一只鸟,一只喜鹊,黑白的经典,像卫兵一样,机警地站在避雷器上,为我站岗。它的巢就搭在我窗外的梧桐树上,它每天都陪伴着我,我起床,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鸟鸣。我巡视,它在我头顶盘旋。我说,你好,它就回应我嘎嘎声。
那天午后,我亲眼目睹了那只鸟飞落在高压线上,瞬间被高压电击中,我将它抱起,紧紧搂在怀里。它还是温热的,我的心里盈满了泪水。
当一道彩虹挂在天上,我将它埋在梧桐树下。小院披上了霓虹,变压器、绝缘子,都生动了起来,它们不再是坚硬的设备,是蓬勃柔软的生命。这时老师傅在身后喊我吃饭,因为没有菜,老师傅烙的葱糊饼,就是在院里挖的葱根儿。墙根儿那一行小葱被大雨淹死了,老师傅把葱根儿洗净、切碎,拌在面粉里烙饼。我咬一口,真香,刷拉一下眼泪下来了。
我想把这些细节呈现出来,把这些美呈现给更多的人。我想写。就这样,忍受变成了坚持,坚持变成了享受。
<b>记者:我注意到,您的作品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慢节奏、大量的细节。是您在基层的坚守,凝结成了这种“慢生活”的诗意,还是想以诗人的姿态,有意地在一个偏僻的变电所保持跟这个世界的疏离?
黄:</b>其实我想当过诗人。在太原铁路机械学校上学时,我把图书馆里所有的诗集都借过了一遍,没有我没看过的,上世纪80年代,诗歌红火。在校园,18岁的人,都是诗人。我的第一首诗歌发表在校报上,写的是思乡。
写诗要有激情。性格使然,我向来妥协、内敛,工作以后,我过的是平淡的日子,买菜做饭,做小女人,好在有小说。这也就决定了我写小说的内容:底层的,琐碎的,小人物。我写身边熟悉或者曾经熟悉的人物,写他们的喜怒哀乐,不去想那些不朽。
<b>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小说创作的?
黄:</b>有一天,我心里有创作的欲望,又觉得诗歌、散文都装不下,觉得应该像讲故事一样讲出来,就这么写了第一篇小说 《念想》。写了一个人的变电所,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师傅,他的忠诚、责任、不舍和他的无奈、遗憾。写得很稚嫩,有些四不像。 《中国铁路文艺》编辑在卷首语是这样介绍它的:毛茸茸的质感。
因为有了文学陪伴,我反而喜欢变电所简单、缓慢的工作,它让我沉下去,与自己内心对话。坐在通勤列车上,坐在长途大巴上,我的耳朵在听,各种腔调;坐在一个人的控制室,思绪可以上天入地。休班时,就去写吧。之后有了《花束》 《正月》 《买媳妇》 《碎碎念》等一系列农村题材的短篇。
“你越写,越懂得写。这是学写作的唯一方法。”这是海明威说的。去观察,去记录,去叙述,感动着他们的感动,快乐着他们的快乐,终于发觉,我有写不完的生活。这个简单的环境给了我一双观察细节的眼睛。
<b> 记者:您的小说语言非常细腻,有女性特有的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对场景的描摹,还有大量民俗元素。比如《拜年》,贴近现实,地域感、画面感很强,是不是跟您的童年经历有关?
黄:</b>我非常感谢上苍没有把我降生在城市里,没有把我降生在显贵之家。它把我投放在河北香河那个叫兴隆庄的小村子里,400多口人守着那条叫青龙湾的河。我的童年,那些无缘无故的快乐,都与这个村子有关,那些黄金般的记忆,是耳濡目染的民风民俗,它浸到我的骨血里,让我的灵魂得以滋润、舒展、灿烂。
我小时候的年,从腊月就开始准备,吃食自不必说,就说一言一行,都是祈福。母亲老早就嘱咐我们,要说吉利话儿。记得那年过年前,隔壁的王大爷死了,我大哥带着我去看吹鼓手,回来后,我大哥一脸兴奋,跟母亲说:“妈,他家请了8个吹儿,赶明儿我爸爸死了,我请16个吹儿。”我母亲哭笑不得。
民俗是文化,是我们的根,我们在这些民俗中体味成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像莫言的山东高密,像贾平凹的陕西。写农村题材的小说,自然就牵涉到风土人情、民俗风貌。这需要日常积累和知识储备,需要提炼升华。
我的童年就是在听故事中长大,我爷爷、我父亲都好讲古,夏日傍晚乘凉,就是听村里老人们讲故事。我父亲给我讲的故事很好听,他加进很多细节,加进很多想象。他讲牛郎织女,他把牛郎比喻成他自己,我妈就是七仙女,我姥姥就是王母娘娘,那两个一男一女的小孩子,一个是我哥,一个是我。话锋一转,他讲王母娘娘的娘家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讲她的身世。
地域文化是不能忽视和小看的,在我的短篇小说 《今生》里,我写了 “爷爷”的一场葬礼,从 “哭”开始, “哭”也成了贯穿全篇的一条线。农村死人,“哭”是一场戏,小孩子们都蜂拥着去看“哭”,哭很有学问,怎么哭,哭什么,都很讲究。在哭中,各种人物,各种心态,百态丛生。通过这些民风民俗,告诉孩子们,什么叫 “了”,什么叫 “宽恕”,什么叫 “感恩”。因为我写的都是我熟悉的,写的是我的那一亩三分地,就比较得心应手。只有在血液里蒸腾过了,才能够贴着人物写。虽说写小说是讲着别人的故事,但那个别人是对话,是你跟这个世界的对话。
<b> 记者:民俗元素对小说的主旨体现起到什么作用?
黄:</b>以 《拜年》为例,小说是通过一个小女孩的视觉,使拜年这件事变得新奇而快乐。农历大年初一,她跟着母亲、新嫂子去村里拜年。因为村子小,大年初一,家家户户的小辈都出动,给每户长辈们拜年,可以想象,那场面很壮观的,这一天就是在拜年中度过。小说从村西头开始,选了有代表性的几户:外出打工的儿子没回来过年,老太太心酸;儿子在外面发财了,把小孩带出去上学,可小孩却融不进其中;没有儿子的孤寡老人,因为旧的传统观念不容许他在女儿家过年……这里有 “临时夫妻”现象,有竞选村干部的矛盾、新旧传统的冲突,其实就是映照当代现实的生活与情感,这使小说没有失之简单。这中间我穿插了传统风俗,小说的调子和煦,将年的气氛烘托得生动活泼。小女孩家里的灯、芝麻秸、窗花、红包,还有磕头、祝福,恰恰透过细细碎碎的这些过程,小女孩懂得了礼仪、安详、和善、感恩。
正因为有了这些民风民俗,才有了一个家庭的美、一个村庄的美,生活是充满美好和希望的。正因为有了这些小温暖,才汇聚成为大温暖。
<b> 记者:作为一名普通的铁路职工,作品一再被《小说选刊》选登,得到文学界的充分肯定,非常难能可贵。能不能谈谈这个过程?
黄:</b>2008年 《小说选刊》第8期选登了我的短篇小说 《亲爱的家》,写的是 “分家”。在我老家有这样的习俗,儿子成家了,就要分出去单过,另立门户,一个 “大家”又分出去好几个 “小家”,枝枝蔓蔓的如同一棵繁茂的大树。
《小说选刊》编辑是这样推介的:“《亲爱的家》礼赞了这样两位老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化作光和热,照耀我们,温暖我们;在他们中年的时候,他们化成音和符,激励我们,鞭策我们;在他们老去的时候,他们就化成一棵苍老的树,用自己所有的根须和枝叶,牵挂我们,想念我们,滋润我们……”
<b>记者:能不能讲讲作为素材的真实生活,进入到您创作过程的一个转变?也就是说,能不能为我们呈现一个生活与小说之间的转化过程?
黄:</b>那年中秋节,我回到家,看到母亲擦拭墙上的相框,一个个玻璃相框里,镶嵌着我们全家人不同时期的照片。我同母亲一张张检索着——就是这张,我第一次照相:在我们家院子里,母亲坐着,我和大哥站在她身后,背景是老枣树。娘仨的表情都很怪异,母亲刚哭过的眼泡肿着,大哥的脸拉得很长,我的嘴巴咧着,像笑又像哭。那时我还上小学,身着小碎花的上衣,毛毛辫子一前一后搭在肩上。那是个特殊的日子,那天我们家分家,我母亲心情特别复杂,难以割舍。赶巧来了一个照相的,母亲就说:给我们照一张吧。她当时认为是按人头收钱,没舍得照大的全家福,就要求照进她大儿子和小闺女,就此留作分家的纪念。
再仔细端详这张照片,我心里一下子涌出好多的想法:家是什么?是一盏明灯,让我们在无边的黑暗中感受温馨,看清方向;家是一支爱歌,让我们在孤独寂寞中体味抚慰,思考未来;家是一棵大树,让我们在凄凉的风雨中享受庇护,勇于前行;家是两位老人,让我们在苍茫的人海中心有所依,情有所系。于是小说里,小女孩美美就感受了什么叫分家,感受了哥哥嫂子、爸爸妈妈的心理变化。家因为 “分”而壮大、而 “和”美、而 “圆”满。写自己熟悉的,就得心应手,写自己感动的,就情真意切,抒写的过程就像河流自然流淌开来。
之后我写 《好日子长着呢》,那对老夫妻,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母亲坐在炕上给自己做寿衣,父亲躺在藤椅上听收音机,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聊着孩子们,聊着村里人,聊着后事,聊着未来——他们的未来,父亲要盖房,盖三间房,给自己住,早年他给儿子们都盖好了房,在暮年他要给自己盖房,因为好日子长着呢。在他们的对话中,透视了农村的现状、五味杂陈的生活、简单而素朴的日子。那关于生死的话题,其实是爱的内涵,传递的是幸福和温暖。
我试着只用对话去表现人物,就像白描,不要色彩,多留空白。我的小说是一幅安详怡然的图画,远远的,就两个老人,却留下深刻意蕴,让人细细品味。
<b>记者:我理解,讲故事并不是您作品的主旨,您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黄:</b>每一篇小说,总有最初打动我的瞬间,之后有了追问和思索。我想用我饱含体温的文字,重构意志、美丽与爱。这种写作是为了改善人心,使人心变得更加美好,这也是我写作的出发点,为了国家民族更美好。
文艺创作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必须的,是创作的基础,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生动鲜活。写作要关注这个时代,关注这个社会。中国的文化是最顽强的文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发生的故事,才是中国味的故事。
我的小说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是因为截取的是我们生活的横断面,是人生的某个瞬间,不是传奇,不是惊心动魄的故事。我希望它是一缕清风,一束阳光,给人们带来的不是震撼,是触动,是抚慰和对人生的理解。
现在传统文化越来越失去力量,没有人来传承,抒写它,是为了保留记忆。通过小说我把问题提出来。这也是一个写作者的担当和使命。
<b> 记者:您认为您的创作历程可以复制么?也就是说,有很多想走这条路的一线职工,您有什么建议、经验提供给他们?
黄:</b>我没给自己设定过目标,就是能走多远是多远,能登多高就多高。在写作上我没有经验可以谈,我只是名业余作者。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坚持发展自己的爱好。我是幸运的,因为走到今天,我是一路被鼓励着的。如果让我对一线作者说什么,那就是坚持下来。我们都在路上,走着走着,不经意间就走出很远了。
近几年,中国铁路总公司宣传部、中国铁路文联始终以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指导思想,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创作了很多精品力作,都是反映一线职工精神面貌、抒写新时期铁路精神的,像长诗写大秦重载、京沪高铁、武广高铁等。近几年,我参与了售票员孙奇、巴山工务人的报告文学创作。随着高铁的建设发展,新的创作任务很艰巨,一听说是抒写铁路人,我的血液就激荡了起来。这种特定题材的创作并没有束缚我,因为我写的是一线职工,在体验中,在与他们对话中,在心灵的碰撞中,我的精神一次次得到洗礼。我写他们,其实写的是我自己,是源于热爱。我爱我笔下的人物,我感谢我笔下的人物。从内心出发,展开人生的种种梦想,我一生要做的是战胜自己,与内心的小我较量,为此无有穷尽。
本文照片由黄丽荣提供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