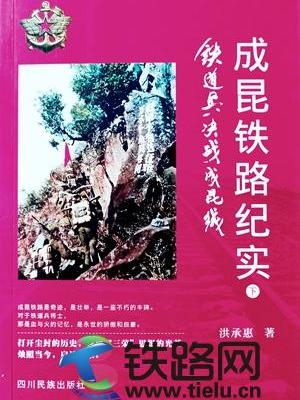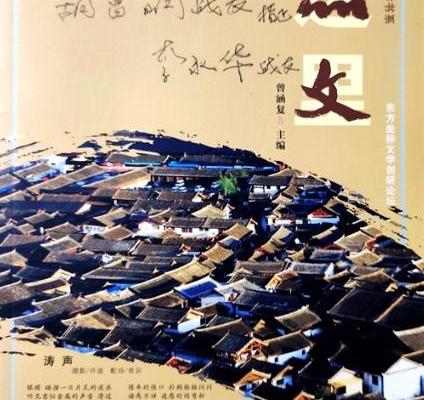肇夕
这是土地撕裂后,凛冽而安静的冰河;这是冰河撕裂后,暗黑的洞见。 “渊默而雷声”,似要随时爆发,仿佛黑铁时代。4个月前,小说家于晓威的丙烯画 《冰河》诞生,我立刻意识到它将成为一幅意义非常的作品,这平静而蕴藏着巨大能量的一角冰河,也许,只有深流在小说家的地理中,才会产生出如此独具一格的能量常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处处机锋。这与小说家本人的思想正好暗合无痕。正如他将自己的一幅以火车为主体的画命名为 《时光中转站》,我觉得,小说家于晓威的画,正是他精神与思维的中转站,是流向小说与诗的中转站,是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奏。如此机缘间,又非常奇妙地成为所有观者的灵感集散地,并产生强烈的共鸣,所激发出的生命力,有些 “悲欣交集”的境界与况味。
此时,这个早在16岁即已握装小说”这把利器的少年,45岁。距中短篇小说集 《L形转弯》的出版,时隔15年。此间经多年的思考、创作与生活的积淀,我猜想,这个性情未变、刀在鞘中,却阅历了人间百态的小说刀客,思想感情的饱和度达到了爆点, “只有把心掏出来,才能好受些吧”。有人说,诗是最高形式的小说。而于晓威的画,正蕴含着诗与小说双重的向度。事实亦真如此,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这属于诗人的激情,是无法用小说的语言去描述的,也来不及。更何况,我个人认为,他长期以来的小说风格,都是缓慢、冷峭和偶尔出人意料的。借为 《L形转弯》作序的杨志广先生的观点,那是“关于 ‘帛的断想”,晓威无时不在关注着人与社会,从 《九月的玉米地》到 《孩子,快跑》,从《陶琼小姐的1944年夏》到 《L形转弯》, “为了证明作家的观念”,他已经到达了 “从理念出发,给出答案”的境界。而杨先生却希望他还有另外一重境界,即是 “从智慧出发,不问答案”,那是2005年7月31日。弹指间,经年逝,如同那《孩子,快跑》中少年端午涯的命运,上世纪70年代生的许多人就这么突兀地长成了。相对于互联网世界中当下的少年们,他们的青春期是很古典的,思想启蒙期受到上世纪80年代初各种文艺思潮的影响,文学滋养则可得自古今中外。若非过分苛责,我觉得,这一代的人格普遍完整,思想行为极具现代性。我认识许多 “70后”作家,他们很少惊慌。不惊慌,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领。可惜杨先生2009年离世,无法眼见他对一个小说家的预言正渐变为现实,虽然,这 “从智慧出发”的思想,经过多年自觉地解构建构融合淬炼,杂糅迸发时竟是自然选择了另一出口——绘画。这淋漓尽致地翻越了语言藩篱的行为,不仅体现了 “所有品质中最重要的是你的生命情绪和认知”,更重要的,它使语言产生了再生性。我认为,这是打开于晓威绘画意象的解码锁,也是这么多作家与读者喜欢这些画的根本原因。那些有着强烈小说指征的画,诸如 《城市:一种被包围的性》 《癫狂与伤感》 《致这个时代手工者》《工业时代》 《被反复涂抹的人》 《欲望大街》 《爱情文具店》,白桦树系列: 《父亲的白桦树》 《母亲的白桦树》《我的白桦树》 《矿工与草撤,又如 《九月玉米地》 《故都的秋》 《不顺从的秋》 《红楼梦》 《博尔赫斯小说论》 《时光中转站》 《那些花儿》 《大冰河》,再如 《城市印象》《大隐图》等4个月来50余幅纸版或布面丙烯画,无不透露着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观念。若杨先生还在,我一定会笑对他说:先生,晓威这个给生命 “断脖的脾气秉性不但没改,怕还是 “变本加厉”地任性了,那些对社会人生的 “固执”看法,绝不打算分什么阶段,而是一以贯之,随时准备对那 “半明半暗、隐秘、交错、混乱、模糊的人性边界”,断喝一声,拔刀而起,剖开真相。所以,当他的画扑面而来时,才会有着不可复制的信息和想象,具有着某种奇妙的能量——既带有个人主义的 “本真性”理想,也附有原生的超现实色彩——正如那令人印象深刻的 《九月玉米地》和 《矿工与草撤。
蒙田说: “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而这事实即是,4个月来,小说家于晓威执画笔,把思想感情爆炸后的火花,快意淋漓地甩刻成一幅幅看似静止、实则运动的画面。而这个过程,最初经由微信朋友圈互相转发,绘画影响竟然扩散于市井与民间,意外地演变成了一场不是行为艺术的艺术。可见,可取的艺术,不问出处。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