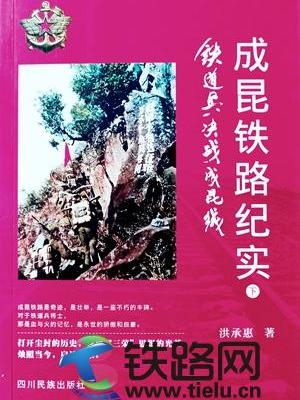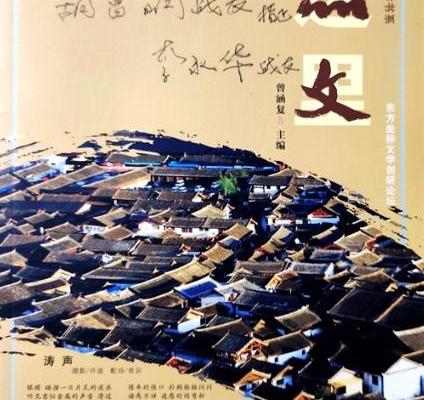戴明浩
本文图片为《黄永玉艺术博物馆电话卡典藏册》内页。戴明浩供图
1月5日,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发行第四轮生肖邮票的龙头——《丙申年》特种邮票1套2枚,36年前,设计新中国首张生肖票——猴票的黄永玉先生,再度出手,一时引发热议。在此,我用这篇文章,回忆曾为黄永玉艺术博物馆设计一本卡册的经历,藉以管窥黄老丰富博大的精神世界、瑰伟多姿的艺术成就和奇特放旷的人生画卷。
机缘巧合,2008年4月初,我走进位于湘西的吉首大学,一睹黄永玉艺术博物馆风貌。在时任该馆副馆长黄毅先生的陪同下,在建筑大师张永和设计的博物馆内,我流连于琳琅的艺术作品和珍贵文物之间,得以立体地感受到黄老斑斓奇绝的艺术天地,为设计该馆的电话卡册寻找思路。
黄永玉艺术博物馆落成于2006年,建筑面积达4200平方米,展厅面积2600平方米。黄老对该馆建设的初衷是 “处理自己收藏多年的珍贵文物和创作的艺术作品”,而吉首大学则以此展示他那极具丰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美术和文学作品,建成研究黄永玉艺术成就和思维特色的重镇,成为探讨社会人生和艺术创作规律的阵地。
序厅陈列着堪称黄氏代表作之一的大型青铜浮雕 《山鬼》及巨画 《采芰荷以为裳》、沉睡三峡江底1.5万年之久的阴沉木和大型黄永玉摄影照等。第一展厅为 “艺术与人生”,内容包括“永不回来的风景”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描画新生活的鬼才” “‘文革’中的 ‘湘西刁民’” “十万狂花入梦寐”和 “黄永玉生平简表”6个部分。第二、第三展厅为 “书画天地”,展有他创作的书画作品,书法作品宣示着他的创作体悟,如 “画画要讲正理,还要讲点歪理,所以我以为中国画家最是诗人,千百年来他们早就在拿形象和笔墨做诗了”。
被列为 “收藏世界”的第四展厅所藏200余件文物,全是天真狂放、气势古拙的宝贝,所属时代上至龙山、仰韶,下迄明清,有中山国陶塑群、唐代石椁、宋代翁仲等。 “我有一批中山国的陶器,看似鸭子,一个一个的,听说故宫有两三个,我有26个,有人劝我捐给故宫,我说哪有把一个军的兵力送给一个连队的道理呢?”让黄老骄傲的这批 “鸭子”也藏于此。
本来,对这位大师,我堪称耳熟能详。参观过博物馆后,我有了更真切的触动。返回长沙后,按照馆方确定的作品范围,我设计出 《黄永玉艺术博物馆电话卡典藏册》,交付后得到馆方和黄老的首肯。印制后,卡册经常被吉首大学、博物馆和制作方选做赠送贵宾的礼品。
通常,介绍黄永玉的简历是这样的:自幼学美术、文学,为一代 “鬼才”,他设计的猴票和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其人博学多识,诗书画俱佳,亦是诗、杂文、散文、小说、剧本创作的大家,出版过多种画册,还有 《永玉六记》 《吴世茫论坛》 《老婆呀,不要哭》 《这些忧郁的碎屑》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太阳下的风景》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书。
他12岁就外出谋生,流落到安徽、福建山区小瓷作坊做童工,后来辗转到上海、台湾和香港;14岁开始发表作品,最早主攻版画,其独具风格的作品饮誉国内外……后来,他又做过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
如果仅从黄老的一两件艺术作品、一两本著作或是风趣的段子入手,就想管窥他厚重的人生的话,那么,这样的设想太失之轻巧。须对中国近代和当代的历史风云、文化秩序、社会变局有一个大致的掌握,才能勉强进入黄永玉的艺术天地。在这样的前提下,故事的场景可能无数次变化,而黄永玉依旧在那里,叼着烟斗,一脸顽皮。但,旁人看不透他的内心,只因,智慧在他那边。
我曾在2004年一个寒冬的清晨,站在凤凰沱江边,静静地看着黄老的玉氏山房,想象黄永玉。而他仍在热闹的世界里,勤奋地创作,玩命地写自己的自传。
2013年冬天,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终于出版。《朱雀城》仅是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第一部,三卷计80余万字,描写了1926年到1937年前后10余年发生在朱雀城的故事。朱雀城就是凤凰,书中的主人公 “幼麟”就是黄永玉的父亲。90多个人物置身于许多重要历史事件之中,被评论为 “有一种古老的教育培养,作为朱雀城的底色而形成庄严的人文秩序”。
这种底色,在他笔下,铺排出一种矫健的气质,一如他的大写意作品,同样不循章法。翻遍文化史,不会有第二人!各种评论铺天盖地而来,评论家周立民说: “实在不是那种匠人所能写出的,甚至也不是 ‘写’出来的,而是‘滚’出来的……”被问要写到哪一年,他回答了8个字: “天假以年,天必假年1 “还想写第二部,写抗战胜利之后的事儿……还想写第三部,写解放后的事儿,那就有意思了,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了……”黄永玉如是感叹。
而我为之惊叹的,不是书中随意穿插那些陌生的古希腊某先哲怎么说,最令我目瞪口呆的是: “我来曲陈与义的 《临江仙》吧——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幼麟用最弱的声音结尾,及至还原回到寂静的空间;笛声与班鼓、檀板也跟随轻微消失。
写这些字的时候,老头儿坐在北京郊区的万荷堂里,回放出几千里外童年的一个夜晚,亲友们为自己外出谋生的父亲送行场面。那一夜,有高山流水,有汉唐余韵,却发生在湘西大山里……他用白话文写出了千年前的古意。他的文字可以当晋人文字读,可以当唐诗来读,他90年的光阴,淌成一条奔涌的河。
老头儿有不能与人言说的寂寞。正如那本 《比我老的老头》中,他寂寞地说着钱钟书、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林风眠、张伯驹、许麟庐、廖冰兄……都是星星般闪亮的名字。文字中,我看到天人一般的记忆力,他的故事好像在世外。
“唉!都错过了,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故事一串串,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已经痛苦得提不起来。”这样的叹息,是属于黄永玉的。这个 “顽劣”的湘西老头,不知道对着谁骂: “世界长大了,我他妈的也老了。”
他活成了一部历史。我们想要打开来,粗看,全是阔大;再看,觉得还要遭受更多坎坷,才能读懂这份阔大。只好闭上眼,进到他的细节里,看到他迈开少年的脚,背了湘西人的刁蛮和豁达,迎着命运走……
于是,在 “太阳下的风景”里,也想要发现些 “忧郁的碎屑”来。从此相信,这世界有了黄永玉,才变得好玩多了。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