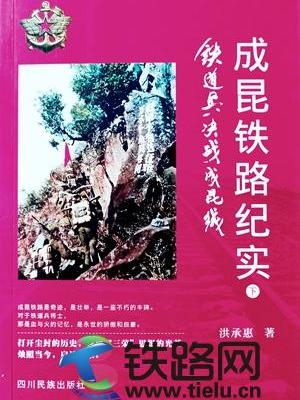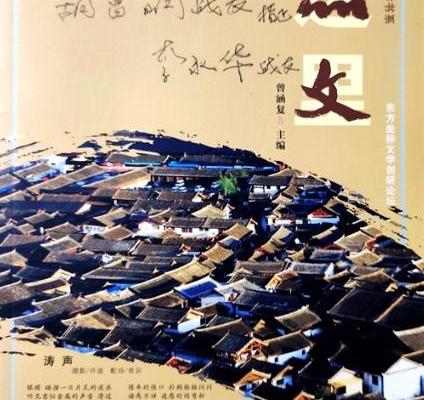戴明浩
所谓的各色美食,乱花渐欲迷人眼。而湘人,仍旧用工匠般的精神,在全心加工辣椒,发现食物里面永恒的春天……
湖南人视辣椒如水和空气。舌尖震颤之后,生活有了被煽情过的幸福,它简单,也美好。而制作辣酱的繁复工艺背后,却是极简心思以及对食物的唯美情怀。
来自美洲的辣椒,在明末 (另说清康熙年间)登陆浙江东部后,再火辣辣地扩张到湖南、贵州、四川等地,最终胜利挺进于内陆纵深。有学者研究指出,辣椒扩张的时间大致吻合“湖广填四川”的时间。 (注:另一说是两路进入中国,西线沿丝绸之路。)
迁徙的人流里,有植物移民——辣椒的身影。我的老友建文,就多次讲述他的先祖靠了一枚辣椒,从江西吉安迁移到湖南湘潭, “累了,就抿舔一下辣椒”,那是祖先的荣光。建文当然嗜辣,湖南人嘛。
“喜辛辣品,虽食前方丈,珍错满前,无椒芥不下箸也”,辣椒溯长江而上几百年后,滇黔湘蜀诸省之人,说到辣椒,貌似惺惺相惜,其实互不买账。都是食辣好手,只好编了顺口溜,你辣我辣大家辣。
时间进入21世纪,祖祖辈辈吃惯的辣椒,猛然在 “美味”大军里面担任起主力军,它助推琳琅美食,让吃货如我辈顿悟:原来,嘴中舌尖,还担负着编织生活美梦的作用。
时代在变,然而辣椒本身,从不曾改变。春天,辣椒苗正积蓄力量,生长。
就像罗大佑在 《鹿港小镇》中唱的: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舌尖美味”甚嚣尘上的当下,被调料调制出来的 “美味”,同样不是味道的真实面目。
这是确凿的现状。在湖南,辣椒依旧被找回原味,成为美味,而非调料。它们是一坛鲜艳的剁辣椒,是一篮在阳光下暴晒的白辣椒,也是屋檐下一长串干红辣椒……
相对于湖南其他地方的辣椒加工工艺,永丰辣酱属登峰造极的作品,它穷尽了辣椒的精细味道,吸纳了几类作物的绵冽气韵,其鲜美无法形容,而辣中带甜的滋味幽幽然扩散,化作周身的通泰,最终让人深吸一口气:好辣酱!
咸丰年间,位极人臣的曾国藩将永丰辣酱带往京城,辣酱备受皇帝喜爱。从此,永丰辣酱被列为贡品。100多年后,2007年,永丰辣酱取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它的产地、配方、滋味和功效,属于湘中盆地,属于双峰县城所在地永丰镇和不多的几个乡镇。
每年入夏,双峰人开始作准备。肉质肥厚、辣中带甜的灯笼椒是它的主要原料;瓷缸装满山泉水,待太阳暴晒至三分之二;打成酱的小麦、黄豆、糯米按比例在不同时段加入;各个环节的衔接要一气呵成,否则辣酱可能丧失自然的甜度。九个环节,几十道工序,开始晒泉水的时间、小麦发酵后晒干的时间、水洗发酵小麦的时间、小麦磨成粉后与 “熟水”混合的时间、辣椒磨碎后与酱胚子混合的时间……几十个日子的暴晒。时间越长,辣酱越香甜。这样的繁复,我想起曾国藩 “屡败屡战”的典故,也想起德国人的工匠精神。
永丰辣酱,有人类的恒心和敬天畏地的情感。一些人躬身于太阳下,引阳光催化,飘作酱香。正如韩国电视剧 《大长今》里面,女主角发现花粉的秘密。食物的美味,需要工匠般的虔诚之心,方可创造。
双峰县地处湘中,明显的大陆性气候,适宜于辣酱原料作物的生长,永丰辣酱是属于时间的艺术。而盛行于湖南西部的灌辣椒,油炒食用,清香酥脆的味道,可当空间造型艺术看待。
山地民族自有其多姿多彩的生活习俗,分布于武陵山脉和雪峰山脉的苗族人口近200万,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饮食文化,同时,也受贵州饮食的影响,增加了对香辣脆味觉的追逐。
灌辣椒,顾名思义要往辣椒里面填入各类食材。不同的县份又有区别。吉首一带叫酸囵辣子、张家界的辣椒包糯米又叫鱼儿辣椒、新化灌辣椒叫糯米粉辣子、绥宁灌辣椒又叫通辣椒……优质辣椒之外,填充物有所区别。为何?莫非先民从山地层叠、白云环绕的空间变化悟出?让每一个辣椒暗伏机趣,就像苏州人 “造园”一般,寓意重重。
湘西的土家族多用红辣椒制作灌辣椒,取其颜色之艳;而位于湘西南的城步、绥宁却爱用青辣椒制作,择烈日到来,把辣椒烫水暴晒一天,晒白后制作,最终得到金黄色的灌辣椒。
值得一提的是城步灌辣椒,它是城步婚庆宴席上最有特色的佳肴,当地人叫它香辣椒、香辣子,特色就是辣脆香。进入农历七月,那里家家户户开始制作:挑选刚摘下的大青辣椒,快速在开水中烫软,再用剪刀在椒腹开一道小口,挤出辣椒籽;填充料有嫩香椿芽、葱、蒜,拌以豆腐渣、糯米粉、五香粉和适量食盐;塞入后,将辣椒开口合拢。经几个大太阳天晒干,干燥收藏,就成了香辣椒。食用时用油细炒,非常讲究火候,要保证辣椒肚里的糯米粉熟透。出锅后,待稍冷却,闻之清香四溢,视之外焦里嫩,咬之松脆可口、鲜美无比。
辣椒是什么味道?它不是一股脑儿的辣。在湖南,它可以是一门繁复的波普艺术,雕刻出时光永恒。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