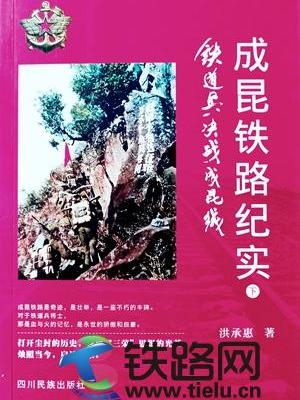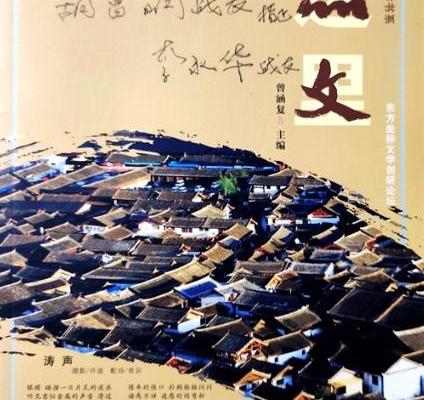田绵石
记得老家小院正中有一堆盖房剩下的石头,一直没舍得扔。1976年唐山大地震,4岁的我站在这堆石头上看着院子里裂开了一道地缝,咕嘟咕嘟地直往外冒水,觉得又新奇又好玩。这堆石料当时派上了用场,被用来盖了简易抗震棚。我们一家在这个棚子里度过了半年多的时光,来年开春才搬回了正房。
正房前面是块空地,母亲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小菜园子。刚一入夏,等不及西红柿和黄瓜完全长熟,我就迫不及待地扎进又闷又热的秧架子里扫荡,钻来钻去,被菜秧子划得浑身刺刺痒痒的。好不容易寻见一个熟透了的,便摘下来赶紧在衣服上蹭几下,一口咬下去。自然长熟的那股纯正味道伴随着汁水,一下子盈满口腔,直奔腹中。
后来,院子里的抗震棚拆了,在原处盖了一个猪圈。那年开春,家里买了只小猪仔,开始第一次养猪。我最喜欢干的事就是蹲在圈门外边发呆,看着猪甩着大耳朵吧唧吧唧地吃猪食,有时看得自己都直流口水。这猪养到半大不大时,生了病,站不起来了。当时母亲很是心疼,让村里大夫来了好多次,给猪看病打针。猪倒也很坚强,一直在努力与疾病抗争。过了半个月,猪终于康复了,又开始津津有味地甩着大耳朵吃东西了。
小院里的那几棵树,一直伴着我成长。房前有两棵柿子树,深秋初冬,满树的叶子落光后,树上只剩下红红的柿子在枝头随着秋风摇曳,在蓝天的映衬下,就像一个个小红灯笼。小棚子边上还有两棵樱桃树,入夏时节会结满白樱桃,个头小小的,甜中带酸。每天我都会到树边摘下一捧,然后四处转悠着吃,很是快活。
院子里最高的是那棵香椿树,每年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是全家吃香椿的好时节。香椿炒鸡蛋、香椿拌豆腐,或者用水焯一下直接凉拌,如果再撒上一些毛虾拌一拌,更是美味。这棵香椿树现在快50岁了,有一人多粗,就连从根部酿出的小苗现在都已长成了大树。这棵老香椿树就这么一直伫立在院子里,树皮已经斑驳脱落,但年年春天发芽吐叶,供人们采食。前些日子回去,二伯说该找人修剪一下高处的老杈了。
我家过堂屋的后门有几级大青石做的台阶,下了台阶,是爷爷奶奶的院子。爷爷好干净,二伯又喜欢侍弄花草,后院被弄得特别雅致。
后院最南头是一块不大的菜地,沿墙栽了一行夹竹桃。潮湿的夏季,后墙青砖上经常长满了湿滑的苔藓,我们没事就爱去那里抠着玩,从墙上捏蜗牛,有时还能看见蘑菇从墙后的草堆里钻出来。
过了这块小菜地,就是二伯侍弄的葡萄藤,从猪圈边上的矮墙爬出来,沿着支架,悬在中间的便道上。夏末初秋,葡萄还未完全长熟,我们小孩子们就有些急不可耐了,总想偷偷摸摸地揪几个尝尝。爷爷坐在屋里,老眼昏花的,替二伯看守着葡萄。我们瞅准时机,先从过堂屋后门溜进后院,弯腰低头,蹑手蹑脚地躲在那堵矮墙后,探头探脑。如果屋子里爷爷没有向这边张望,我们就悄悄探出身子,伸手去够架上的葡萄,往往在这时候,就会听见爷爷在屋子里喊着: “小兔崽子们1吓得我们赶紧缩回去,弯腰低头又退回到过堂屋,等待时机再次出动。这出爷孙之间的 “游击战”年年不断。葡萄一季一季熟,爷爷一年一年老,直到有一天,爷爷喊不动了,我们长大了。
中秋,葡萄熟了,紫色的,一串串吊在藤上。这时候,爷爷总会给我们这些小崽子们分些葡萄吃。
经过葡萄架,便道两边又是菜地。这条便道虽然不长,但爷爷把它拾掇得很干净。便道两侧栽种着马青菜花、大丽花、鸡冠子花、夜来香、茉莉花。走到这条花茎的尽头,是房前的平台。临近窗前的平台处摆放着大型的盆景和花卉,那是二伯侍弄的。每到秋季,各色菊花把小院装点得很是缤纷热闹。
平台边上有一个压水井。每当放学从外边玩回来,又渴又热的时候,我就跑到这里用水瓢接满压出来的凉水,瞪着眼睛大口大口地喝下去,喝完直憋得赶紧深吸一口气,然后抹抹嘴巴子,满意地径直走进爷爷奶奶的过堂屋掀锅盖、翻盆子,四下找吃的。临近房前的东墙边上,爬满了一墙的金银藤。夏夜,金银藤芳香四溢,我们这些孩子们总要采摘一些,捏在手里,顶住鼻子,闭上眼猛吸几下,直到把花捏得没形了,再去摘新的。
我离开小院快30年了,每当回忆起自家老宅那个院子时,脸上还时常浮现出别人难以觉察的满足与惬意。那份温情,难以言表。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