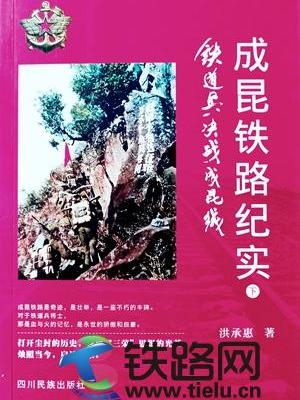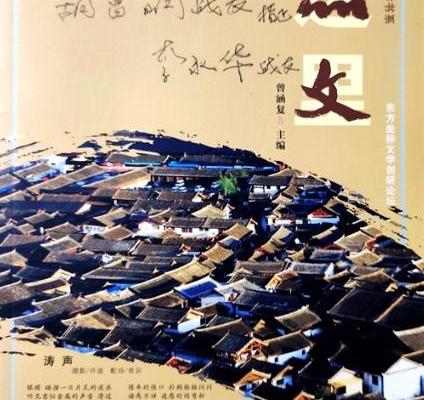陈国庆
听到商合杭高铁建设的消息,我的心情有些激动。家乡通了动车后,我回家就只需要几十分钟,路途不再漫长了。
我在十字铺站工作时,小站刚刚建成。尽管是普速铁路,但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扶老携幼来看火车。那情景如同铁凝的小说 《哦,香雪》一般,至今回忆起来仍觉得亲切。
一大早,天还没大亮,东方刚现鱼肚白,大伙就准备从各家中动身了。一盏盏昏黄的灯下,映着一张张因激动而通红的脸,连墙上的影子也激动得发抖。小孩子最是闹腾和兴奋,褂子扣错了的,裤子穿反了的,都有。小姑娘家头发梳得水亮,扎着的红绸绳如杜鹃花一样火红,穿过年才穿的新衣服,戴赶集才戴的银饰。路边小草上挂着的露水打湿了乡亲们的新布鞋,不管,脚步依然飞快向前;丛林中的荆棘划破了手背,不怕,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看火车去。看火车——如同看一场大戏,如同赶一个大集。
连狗儿也知道这是一个快乐的日子,一路狂奔,一路狂吠。
小站的月台上站满了我的父老乡亲。从左到右,里外三层,密密匝匝。从运转室的小楼上面俯瞰下来,全是黑黑的人头。那场面,真的很壮观。小站的站长带着好几个工友在维持现场秩序,生怕有点闪失。8时05分,太阳升起了,小站第一趟火车也来了。火车喷云吐雾,呼啸而至。对了,那时机头还是蒸汽机车。司机拉响一声长笛,“呜——”巨大的吼叫声,把所有的乡亲们都吓着了。有的小女孩都被吓哭了。只用了几十秒钟,火车就在乡亲们的目送下,消失在山那边的尽头。
然而,火车留下的力量还在震荡山水,还在鼓动人心。之后,大伙们欢呼着,议论着,虽然没有说“火车站立起来跑肯定更快”这样的笑话,但大家数了有多少节车厢,有的乡亲还为多一节少一节而争论哩。不管怎么说,来看火车的乡亲们俨然已经是 “见过世面”的人了,他们可以回去给那些没有看过火车的人吹一吹火车是啥样子的了。现在想起,我的眼睛依然湿润。
我那时在小站,职工人不多,包括站长在内一共有十八个。我们都戏说我们是 “小站的十八棵青松”,但是也有两位漂亮的售票员姑娘。小伙子知道姑娘爱花,春天在姑娘的镜子边用水杯养几枝蕙兰,秋后在姑娘的窗台送一盆秋菊,倒也不俗。姑娘们的宿舍一年四季花香四溢,芬芳无比。
我虽然已人过中年,但看着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们旺盛的精力,就像开了盖的啤酒,也想干他一杯,心就年轻了。我开始在屋前种柳,房后植竹——轩窗绕牵牛花青藤,西墙爬山虎满壁……我把小站打理成了一个花园,自己也成了小站的“花圃乔叟”,护着美丽的花木,也护着像花一样的人。每到腊月冬闲,我又当上了 “月老”,站上的小伙子请我去附近姑娘家下聘,也有村庄的姑娘托我给站上的小伙子说媒。一连串的喜酒使我常饮常醉,常醉常欢。闲来无事时,我又上山掰青笋、捡蘑菇,下河摸田螺、钓鱼虾,怡然自得。只见鸥鸟如家养的禽雉,见我来时,也不慌张,依然不紧不慢地在农家的稻田中搜寻,好像认识我了。也有白鹭于空中盘旋,欲下未下的样子。怕是新来的吧?或是还有什么新的要求?但见落下的时候,风把它们头上的一撮长羽,吹得潇洒如神仙手里的拂尘。
一晃就好多年过去了。十字铺站随着祖国的发展,茁壮成长。小站生在农村,长在田畈,有村姑是小站的媳妇,有工友是村庄的女婿,小站与农村融为一体,血脉相连。春天田里的秧绿了,小站也碧色盎然;秋天土地的庄稼黄了,小站就沉甸甸得秋色如画。来往于小站的火车,一趟接着一趟,把和谐的气氛带到天南地北。汽笛声声里,一年又一年。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