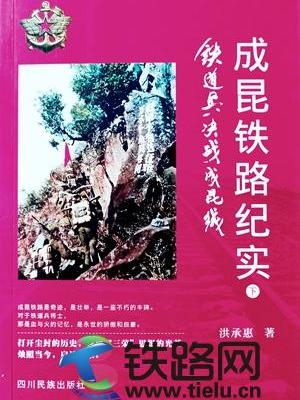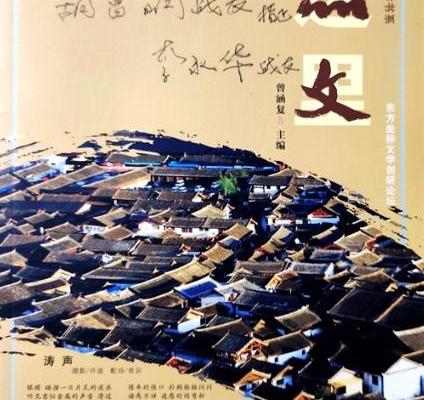陈清
图为2000年后的二道岩站 杨铁军 摄
和小站结缘,缘于父亲的事业,回想起来,整整50年了。
50年前的1966年3月,父亲同他的战友们在完成了贵昆铁路滥坝至双水间一个叫做粑粑店的铁路隧道修建任务后,部分同志接到工程处人事通知,到临管处报道。1966年7月,我的父亲正式成为新组建的水城车务段的一员。
简陋的住房
1966年7月的一天,地处老黑山深处的二道岩站热闹非凡,这天,临管处的火车第一次送职工到车站报道。“要来火车了1十里八乡的汉族和苗族同胞背着苞谷花、洋芋、炒面从方圆数十里的地方早早赶来,就是要亲眼看看据说 “叫起来声音比老虎还大”的火车。临管处的上游型蒸汽机车牵引着几节棚车 “轰隆卤鸣叫着开走后,站台上参观者散去,留下了我们及些许行李,站长告诉父亲,我们的家就在铁路边上。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那个房屋依然记忆犹新。那是一排排用碗口粗细的楠竹搭就的临时工棚,用油毛毡盖顶,四壁全用竹席围就,室内连最简单的地平都没有。在家里,只要你移动脚步,不是扬起尘土就是掀起泥浆,马扎上铺就几块木板就是床了。
半年后,这个家伴随着1967年春天的一场山洪荡然无存,好在那天我跟随父亲睡在了车站的票房。后来的日子,我们和车站的叔叔伯伯只能住在候车室、行李房了。1967年下半年,安顺工务段的轨道车陆陆续续运来了大批建筑材料,夜以继日,人背肩扛,终于在1969年的春节前建起了五六排砖混结构的瓦房。从此,二道岩站的职工有了正规的住房,职工们纷纷接来了分居多年的老人、妻儿,艰苦的环境中有了欢乐的笑声。带家属的职工们利用休班时间,邀约三两个农民帮忙,自己动手,利用铁路边取之不尽的山石、工务段废弃的枕木,在房前屋后建起了简易的房子,房内搭上几块木板便成了厨房或住房。
我长大后,成为了六盘水车务段的一名职工,并先后在且午、乐居、葡萄菁、花赖几个车站工作。那些年住房条件还是非常艰苦的,通常是几个人挤住一间房,但艰苦程度还是不足以在前辈们的面前提及。
20世纪90年代初,新的 “三线”建设开始。几年间,过往的旅客惊奇地发现,小站漂亮了。老旧的房屋或拆建,或穿上了新 “衣”,以往的垃圾堆搬走了,小山包变成了花园,亭台水榭相间。又过了些年,小站就是现在的样子。前些时日,老父亲从海南回来,说想去小站看看。站在新的站房前,连我这个 “老铁路”都大吃一惊,小站早已没有了当年的影子,父亲环顾这个他28年从未离开过的车站,曾经引以为豪的四层小洋楼如今人去楼空。我看到了父亲眼中的泪花和继而泛起的笑容。
小站之夜
傍晚,华灯初上。当夕阳将自己娇美的最后一抹余晖藏到山后时,城市的灯火更加灿烂了。且午站上,除了风驰电掣的列车呼啸而过、让行列车停靠时发出刺耳的刹车声、运转室内值班员不断发出指令的声音外,余下的就只有远处山谷中时不时传来的夜莺啼鸣了。小站的夜色是那样恬静、安详,空气里少了城里的喧嚣浮躁。运转室总是彻夜灯火通明,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各种指示灯光闪烁不停,一派繁忙景象。看着这些现代化、自动化的新设备,还有多少人记得当年小站上那摇曳的煤油灯。
30多年前,我进入了六盘水车务段,认识了我真正意义上作为铁路人的第一座车站——且午站。我的师傅叫黄发启,不一会儿,他就帮我领来了备品,其中就有那盏后来伴随我多年的煤油灯。
小站的夜漆黑而又漫长,让我没想到的是居然没电。我守着占据了大半间屋子的烤火煤堆,怀着至今都无法说清的复杂心情,就着照明的煤油灯光胡乱翻阅着如今早已记不住名字的书,打发这长夜的寂寞。也不知道几点了,邻居师傅家的大公鸡一声紧似一声的鸣叫,把窗外的山雀都吵醒了。煤油灯灯罩被熏得漆黑,灯油早就燃尽,只剩下一丝青烟。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个与煤油灯相伴的夜晚。此后的8年时间,我的大部分夜晚都是在这样的煤油灯下度过的。
与煤油灯相伴的日子
上班第一天,我看到的设备是现今看来几近原始的半自动集中联锁臂板信号机,道岔是手动的。师傅把我带到扳道房旁边搭建的一个偏房内,告诉我这就是灯具房。在一根油乎乎的枕木上一字排开摆放着8盏煤油灯,旁边摆着几个油瓶,这就是我上班后认识的第二种煤油灯了。 “这是生产用灯,同生活用灯是有区别的。”师傅说。扳道员的工作除了准备进路、迎送列车、擦拭道岔外,很重要而且技术含量较高的一项工作就是清洁灯具、准备油料、修剪灯芯、调试亮度、上杆揭挂。师傅说: “清洁灯具的重点是内罩的清洁,油料的准备是要注意加多少才合适,灯灭了机车就不能准确辨别信号,影响行车安全,那可不是小事。”经过师傅示范,我发现的确不是很难,需要的是细致入微的责任心。上杆揭挂就不一样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贵昆铁路,最高海拔就在且午站的2号道岔上,昆明方面的坡道达到12.5‰。臂板式进站信号机高高矗立的电杆会让你不寒而栗。师傅在说话间就爬到了信号机的顶端,我的心底顿时生出几分敬佩。
云南的风有名,但也不光是在春天,秋天的风吹得同样卖力。下午,同运转室联系后抓住列车间隙的空当,我提起早早准备好的煤油灯向信号机奔去,按照师傅的指点,左手提灯,大约30来斤,右手扶梯单手向上攀爬,等到了第一个灯的位置再用一只脚勾住信号机的扶梯,腾出手来把煤油灯放入固定的支架上,如此这般,3盏灯放好后再打开检查窗,逐一对油灯的燃烧情况进行检查,看看灯焰是否合适。第二天,师傅告诉我,昨晚的灯挂得不错。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师傅接着说: “2道出发在正线上,通过较频繁但灯光暗了点儿,进站信号机进侧线灯光被风吹灭一次,是你在关闭灯窗时没密闭好。”看着师傅丝毫没有责怪的意思,我已下定决心,今后再不能犯类似的错误了。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但对于当年在煤油灯下彻夜读书、值守夜班被熏黑了眼圈和鼻孔以及师傅细心指导我上杆揭挂的情景,我的记忆是那样深刻。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