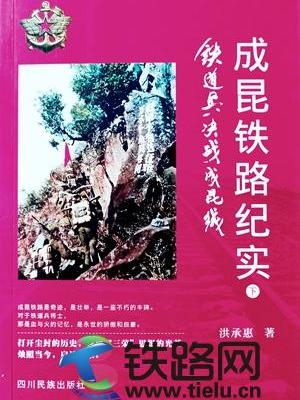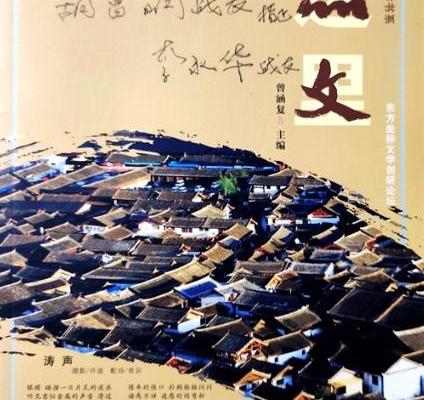张春兰
母亲是一部读不劲写不尽的书,我一直这样觉得。不经意间,我又想起了家里的3位留守母亲。
“你不许进我家,你是谁?”一个小女孩,坐在门坎上,举着锄草的小挖锄,望着拎着行李包的陌生人,正气凛然地大声说。这就是我童年时期看到爸爸回家时印象最深的一次。
那年我6岁。
妈妈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也是村里文化水平最高的女干部。妈妈总是很忙,要出工干农活,要照顾我们三兄妹,要在村里扫盲班当老师,还要调解各家鸡毛蒜皮的小事。晚上,妈妈常常搂着我讲童话故事,讲远方的爸爸。那时,我最爱问的一句话就是:“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总是微笑道: “兰兰,你爸爸在很远的地方修铁路,他也很想我们。”
我8岁那年的冬天,妈妈因为长年过度劳累生病了。爸爸请假回家照顾妈妈,但妈妈的病情始终没有好转。为了兼顾工作,爸爸带着我们来到了他的工地。
我们一家五口住在工地一间 “家属房”。所谓的房子,就是在一个山坡上临时修建的油毛毡房,条件远比不上农村老家,但我们全家在一起,其乐融融。妈妈在这里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后半年的幸福时光。
两年以后,我有了继母。我当时很叛逆,时常和继母争吵,不论是对是错,总是莫名地要护卫两个弟弟。就这样,我和继母僵持了3年,继母包容了我很多。
3年后,我们全家住到了衡广复线工地上。我们住的房子在湖南省耒阳县城郊区的一个小山坡上,依然是油毛毡房。爸爸工资不高,生活难以为继。继母很勤劳,经常打一些零工,以补贴家用。继母对我们的读书生活样样操心,晚上督促我们学习,早上煮好饭催我们起床。我们先后考上了大中专院校,继母一直以我们为荣。我们也从内心感激继母,是她,给了我们另一份难能可贵的爱。
从长沙铁道学院毕业后,我也成为一名铁路建设者。我和丈夫同时毕业,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可是不久,他因工作需要远调西南,我们开始了异地相思的生活。
1995年,我生孩子时,丈夫正在出差,是继母陪着我进了产房。儿子出生17天后,他才急匆匆赶回家。后来儿子练书法、学绘画、上幼儿园、上小学……我又当爹又当妈独自拉扯着。由于铁路施工地点频繁变化,丈夫一年到头很少在家。
2009年春节,丈夫驻守工地,我带着儿子远赴青海德令哈,陪他一起过年。在海拔3000多米的雪域高原,尽管条件异常恶劣,但我们依然掩饰不住团圆的喜悦。为了把这份喜悦与大家分享,农历大年初二,我和儿子随丈夫去工地看望工人,他们像家人一样热情。当他们遥望远方,激动地介绍着那条新建的铁路时,眼前一切艰难困苦和对妻儿的思念,顿时化作飞扬的神采,油然而生的浪漫乐观情愫,深深地感染着我。
返程列车上,儿子指着我们全家福中明显苍老的丈夫,向同车的人炫耀: “这是我爸爸,这条铁路就是我爸爸他们修的。”儿子那天真的话语和那张全家福,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恶劣的天气风化了筑路人的容颜,也雕刻出他们的豪迈精神、男人气慨、父亲形象。这使儿子满脸自豪,也是我由衷的慰藉。
我和儿子哼着 《天路》,那悠扬的旋律,和着列车富于音乐美感的节拍,把我这个留守母亲骄傲、倔强、幸福的情怀,带到绵延不绝的远方,飘上苍茫舒卷的云端。
系中国中铁五局集团机电有限责任公司职工)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