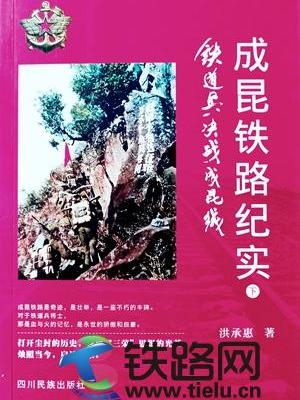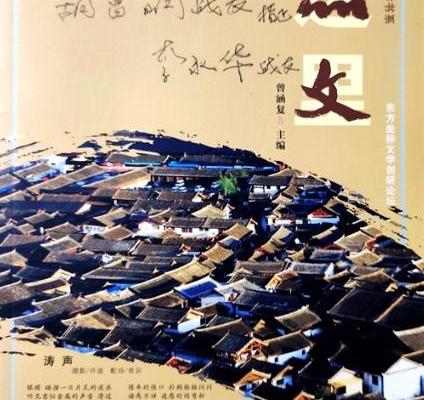亚洪说,雨天不适合听马勒。为什么?我就很纳闷。说马勒的交响乐潮湿,只有亚洪这么说。这是他从指挥棒上体味出来的一种对音乐的感觉。这感觉我没有。他再三强调:音乐,会见。他也叫我音乐会见。我不想见。因我产生不了他所谓的潮湿的那种感觉,我甚至会有困在沙漠腹地焦渴不安的逆反感觉。在天资上跟亚洪向背而立,会见,还会见什么呢?感受的结果一定是南辕北辙。
确切地说,我是个乐盲,我不懂音乐。但他还是要求我,音乐,会见。
不赴音乐会的亚洪已够儒雅、够小资的了。高额,高鼻梁,高高后扬的蓬松发型,架着一副文质彬彬的眼镜。在对近代文人的想象中,找得出很多同类的影子。他会一口英文,也会写一两首现代汉诗,三楼书房内始终放置着一台“Rancilio”牌子的意式咖啡机,压榨着羊粪似的肯尼亚咖啡豆。音乐响起,自然是西洋的古典乐曲,作为背景同时跟咖啡豆焦味的浓香气味,在客人们的鼻底与耳际之间缭绕。科班出身的亚洪,弥漫着咖啡豆香味与柴可夫斯基的音符,蛰伏在温州某一个深巷里,俨然一只沐浴过欧风美雨的“海龟”。于是有文友戏谑他:假洋鬼子。
从广义而言,亚洪是位时尚的新散文作家。行文流畅、轻快、不拘一格。近年,他挂着单反,四处游走于乡村、闾巷,写小巷,写村落,用取景框与键盘记录下时代变迁中即将消逝的时光碎片。在我看来,他写得最出彩的还是多部与音乐有关的专著,像《音乐为什么》《天鹅斯万的午后》,在乐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他的音乐随笔跟他的个人气质已水乳交融在一起,敏锐,前卫。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比较洋气。他的写作经验已把他与音乐厅、大剧院、指挥、乐团联系在一起,与切利比达克,与福莱、瓦格纳、海顿、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这些人名联系在一起。他热爱音乐,甚至爱屋及乌,给自己心爱的书房取了个斋号:水乐斋。那年,岭南归来适逢台风时节,乌云密布,他竟然独自冒着飓风将临的危险,带着块青田封门石驾车来访。我用刻刀在印石上为他奏下一行边款:音乐如水漫过的房子。
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尼采这样说。我接纳了这个错误。拿儿子的话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尽管是一知半解感受着蝌蚪跳跃的力量,但我还是个乐盲,我不懂音乐。但亚洪还是鼓励我,音乐,会见。我拒绝过他:音乐,不会见。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京师爱乐丛书”系列之一的《音乐会见》非常精致,亚洪用了5个乐章漂亮地完成她。马勒、瓦格纳、切利比达克,这些大师的作品,如节庆的灯笼,不,如珠宝大师手掌上的水晶,非常纯净、专业、晶莹剔透地穿在一起。亨德尔说,音乐的目的是使人高尚起来,于是我开始了阅读。
“定音鼓熄灭了,小号熄灭了,长号熄灭了,大号熄灭了,竖琴熄灭了,单簧管熄灭了,只有几把弦乐器拉动着,细如游丝,像死前呼出的最后一口气。我望着台上的人,不敢呼吸,场内听不到任何音乐,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我都要哭了。”这是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德国指挥家帕沃·雅尔维演绎马勒《第九交响曲》的情景结尾,也是乐评家郑亚洪在《苏州,法兰克福,马勒》一文中所描述的结尾。马勒要死了,他要最后看一眼他的故乡,看一眼依然茂盛的树、花、草,看一眼他的女人阿尔玛。
面对弥留之际的马勒,亚洪说,马勒对生的渴望、对生活的眷恋,被小提琴毫无保留地宣叙出来。
亚洪看这场演出、写这篇文章已经过去8年了,我不是被马勒、被帕沃·雅尔维所感动,因为我根本不熟悉他们也不懂得他们,我是真心被亚洪诗一般的文字所感染,被亚洪小说一般的描述所感动,他的表述如此宁静,如此优美。他在观赏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的时候,看到指挥家切利比达克,突然来了个大转弯,放弃了冲刺,由慢变成彻底的慢。因为慢,这就是高潮,高潮中的高潮。
当读到这些章节,我禁不住暗暗喝彩:太棒了!文字链接着音符,令人心扉震颤。我联想到人的一生,自己的一生,慢些,再慢些,这是人生的高潮,高潮中的高潮。《第五交响曲》是柴氏“悲怆三部曲”中最复杂的一部,而终曲又是最具矛盾、最不平衡的一个乐章,表现生命、欢乐和幸福的音乐十分动人,让无数历经苦难的人们,备感亲切。
由衷地要从内心伸出一只瘦弱的手,握一握亚洪。觉得没有理由再说:音乐,不会见。
古典乐评以外,巴洛克音乐、尼德兰音乐、印象派音乐、浪漫或后浪漫派音乐,期待亚洪有更多的尝试与涉足,在音乐领域的抒写方面遨游得更广阔、更辽远。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