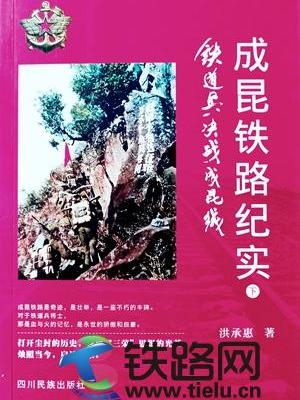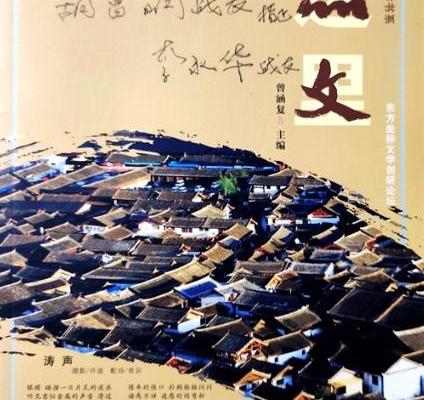把流浪理解为“生活没有着落,四处漂泊”,只能是一半正确,一半纯属偏颇。 比如三毛写的《橄榄树》,她的流浪显然不是“生活没有着落”,而是“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涧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还有还有,为了梦中的小毛驴”——最后一句,后来被人篡改成了“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偶或地,我会去外面走一走,我把这种走一走,也视作一种流浪。很喜欢这个词。原因乃在于它是如此地切合我外出时的心境。这种心境,用了“旅游”,哪怕用“旅行”,就破坏殆荆而且,“旅游”、“旅行”未免布尔乔亚了。这是一种不错的情调,不过,我颇不喜欢这种情调。事实上,我也不具备这种情调。
很显然,我渴望流浪,渴望在流浪途中,看见天空飞翔的小鸟,看见山涧清流的小溪,看见宽阔的草原,和那梦中的小毛驴。若要找寻流浪的意义,我来告诉你:全在这“看见”里。
就为了这“看见”,人生难道不值得去流浪吗?
这么多年来,我的行走,端的是为了这些“看见”。然而,除了这“看见”,我还意外地收获了一种东西——在茫茫人海,在萧索偏僻之地,我看见过一个人,一个像我母亲一样的人。我还看见过一个逝去的人,他与我的父亲同名。
二〇一四年十月底的一天,在河南台前县一个村庄里,一个老太太从我对面向我走来。她向南来,我往北去,村庄里的巷子,仅容得下两个人的并行。我停下脚步,让老人家过去。突然,老人一个趔趄,我一把将她扶住,这时,她转过脸来,这一转脸不要紧,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不假思索地竟然叫了她一声:“妈!
老太太笑了。她说:“我不是你妈,你认错了!
我没有笑,我笑不起来。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也许应该叫情感),然后我说:“我送您回家!”老太太说:“就这!就这!
推开院门,一棵桃树下趴着一只鸡和一只猫。鸡无动于衷,猫则跑过来冲着主人“喵喵喵”地叫着。
老太太要我坐下,我说,不坐了,还得赶路呢。我问她,您的脚没事吧?她说,没事。我说,那我走了。老太太在我身后嘟囔了一句:连口水也没喝!我转过身想冲她一笑,可泪水却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
有一年我回家,刚到家,就接到单位电话,不得不往回赶。临走时,母亲说的正是这句话——“连口水也没喝!
走出村外,是大片的麦田,一眼望不到边。这次外出,有一个奇妙的发现:几乎每一家的麦田里都有几座坟。当地百姓告诉我,他们这里没有公墓,家中的人过世后就埋在自家的田地里,天长日久,麦田地里的坟头就多了起来。
行走在麦田间的那条土路上,我的心情颇不平静。不时有农人从我身边走过。我不再看他们,我害怕看他们。我只把目光对准麦田,那绿茵茵的麦田,像极了城市里的草坪。在这个萧索的村庄里,在这片灰蒙蒙的天空下,唯有这片麦田给我一点好心情。
一只鸟从头顶飞过。但这不是三毛眼里的那只天空中飞翔的小鸟,也不是我心中的那只天空中飞翔的小鸟。这只灰头灰脸的小鸟,一如此时的天际,一如我身后的村庄。但这只鸟忽然落了下来,不偏不倚地落在了一块墓碑上。
走过去,那只鸟并没有急着飞走,看来这只鸟也成“老江湖”了——人固然可怕,但不拿枪的人绝不可怕。据说,这是鸟语。直至快接近它时,它才“扑哧”一声飞走了。
墓碑是一块普通的墓碑,上面刻着“先考张叶茂之墓”。其名字,与我父亲仅一字之别。我父亲也叫张叶茂,但我父亲名字中的业,是事业的业。
可惜,没有相片。
此时,我的大脑已与这片天地没了区别:灰蒙又混沌。这次寻根之旅——濮阳,乃张姓之根,张公艺墓便在台前。
我想象不出这个叫张叶茂的人,他的长相会是个什么样子?我想知道的是,他的老伴,他的孩子现在哪里?
我在墓碑前给这个与我父亲同名的人点上一支烟,略表我对他的敬意。在这个人的世界里,同姓都是“五百年前一家人”,何况还有着相同的名字呢!
走出墓地,来到田间那条小路上时,正巧来了一个人。他很好奇地看着我,然后对我说:“你是他家亲戚?”我摇摇头:“不是!”他更好奇了:“不是,你去看他墓干吗?”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说:“你认识这墓主人?”他说:“我父亲!
我笑了。我说:“天啊!”他略显紧张,烟头都快烧到他手指头了,还夹着不放。我说:“没啥,我路过此地,看见大多数人家的坟头都没有立碑。出于好奇,我过去看了看,竟看见你父亲的名字与我父亲同名。”他顿时睁大了双眼,说:“不会吧?”我说:“我父亲的名字叫张业茂!”他终于放松了警惕,露出了笑容。“去我家喝酒吧,咱们就是兄弟啦!”他双手不停地搓着自己的衣服,激动得脸都红了起来。我说:“谢谢兄弟,下次吧,我会再来的。”他说:“你下次真会来?”没等我开口,他就喜不自禁地感叹了起来:“缘啊!缘啊!你说你说,这天底下咋有这么巧的事呢?”我说:“你母亲可好?”他手一伸,向前一指:“看见那个冒烟的房子没有,村南头那一家,就是我母亲住的。”
“院子里有一棵大桃树的?”
他又一次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你怎么知道?”
我回说:“刚才路过,跟老人打了招呼。”我没有跟他说,他的母亲像极了我的母亲。
“唉!”他长叹了一口气。“母亲百年后会有麻烦的。”
我不解:“麻烦?”
他说“我母亲先前结过婚,丈夫死了。与我父亲结婚时,母亲有言在先:她百年后要与前夫合葬。父亲去世前把我们兄弟们叫到一处,讲了母亲与他的约定,要我们尊重母亲,不要同母亲那边所生的两个儿子争抢,闹笑话。”
说完,他哭了。
止住了哭,我问他:“为父亲在另一个世界里孤独而难过,是吗?”他说:“不!为没有了母亲!
我抱住这位陌生的兄弟,我伏在他宽阔的肩头,突然哽咽。他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此时的忧,早已成为我心中的痛了。他能明白我的哽咽吗?
谁说人的命运各不相同?在这位老实巴交的兄弟面前,我看见了命运,看见了命运这家伙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啊!
我没有看见那个叫张叶茂的老人的相片,我也没有问他:墓碑上为何不放一张老人的相片?放有放的道理,不放也有不放的道理。世间事不会只有一个道理。
这个叫张叶茂的老人长相如何,的确不重要。这个世界里同姓同名者大有人在,一点儿也不奇怪。尤其中国,张王李这三姓,重名的便不计其数。谁能说,姓名相同,命运就必然相同呢?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