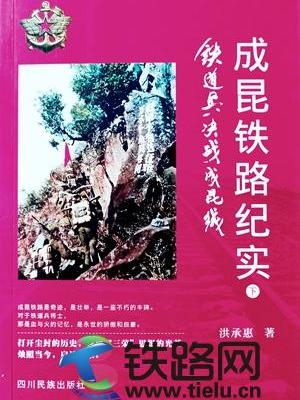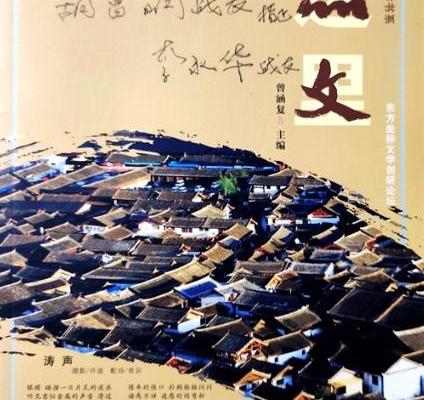■陈 纸
喜欢看话剧,《厄尔尼诺现象》《董竹君》《恋爱的犀牛》《第一次亲密接触》《大将军寇流兰》,都是难忘的,却很少读剧本。订了几年的《世界文学》杂志,遇到刊载剧本,便绕道而过,只是觉得,剧本嘛,不呈现在舞台上,琐碎得很,抽象得很,不好理解。
巧得很,最近一次读剧本,与蛙有关,是莫言的《蛙》。莫言的《蛙》,前面大部分是长篇小说《蛙》,后面小部分是剧本《蛙》,当时觉得这样同题却不同体裁的文本很有趣。
近读王彬发表在《中国作家》2016年第11期的近4万字的四幕五场话剧,也与蛙有关,叫《蛙地》。读了《蛙地》,则是另一种感受:恬静的夜里,喧嚣的客厅,变异的青蛙,化身为人,蛙声四起,却道尽世相人心。
剧本《蛙地》的故事很简单:孙玉尊是某化工集团总经理,他在生命即将结束时立下遗嘱,将财产分配给妻子和3个儿子。但不知何故,遗嘱提前泄露。孙玉尊偏爱大儿子,让他的妻子和二儿子、三儿子,甚至家里的阿姨都愤怒了。他们出于各自的目的,纷纷将矛头指向孙玉尊。还是变异的蛙们知晓其中隐情,他们聚集到孙玉尊的家里,见证了孙玉尊遗嘱如何执行、围绕遗嘱发生的家庭内部惨烈的争夺战……其实,人性的幽暗还不止于此,因环境破坏对蛙的祸害、蛙与人的命运结局……却能引发读者更幽深、更庞杂的思考。
正如《蛙地》剧作者所说:“旧的主人走了,新的主人来了,小洋楼还是那样,只是在容颜上堆塑了几道波痕,在人们的心底注入些许沧桑。”而那些聒噪的蛙声,“是多彩的,诸如愉快的、忧虑的……”全是人的化身,亦是在物欲面前人格的体现。与人相对的,“异化”了的蛙们,却成了正常的人,在旁看懂了人的“异化”行径。
王彬笔下的这些蛙,虽然是异类,但是会说话,而且走上了舞台,与人类一起,共同演绎了一场人生的悲喜剧,甚至,蛙也成了人类悲喜剧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陷入同一种境遇。
对戏剧而言,在传统“现实主义”之外,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表演样式。如果《蛙地》要搬上舞台,肯定要贴上“先锋戏剧”的标签,而且一定能成就一部大戏。王彬这部创作于1999年的话剧,今天读来依旧给人以现实的刺痛与无奈之感,俄罗斯有一句谚语:“在清水里泡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你就干净了。”在这样的审判面前,有谁可以做出肯定的回答?
《蛙地》披着一件后现代主义“解构”的外衣,又穿着一件“建构”意义的里子。后现代的外衣所向披靡,给了剧作者肢解故事的勇气。剧本中,人声与蛙声,戏谑中有严肃,现代与后现代,互为表里,有血有肉。结尾处,“雨声惊天动地而来”,直至“闪电如醉如痴”“蛙声与雷声交织一片”……字里行间,密密麻麻的情绪跌宕与场景变幻,隐藏着剧作者对现实的无奈。
与王彬以前散文、随笔作品中对一条胡同、一棵树、一轮清月的消失都深含隐忧一样,他的写作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这次他的《蛙地》以一次剧本的华美制作,以加缪式的荒诞抵达了痛苦与真诚,以沉静的耐力,完成了更广阔世相人心的描绘、更多变写作手法的跃升。
《蛙地》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