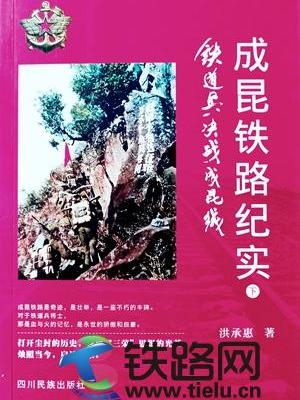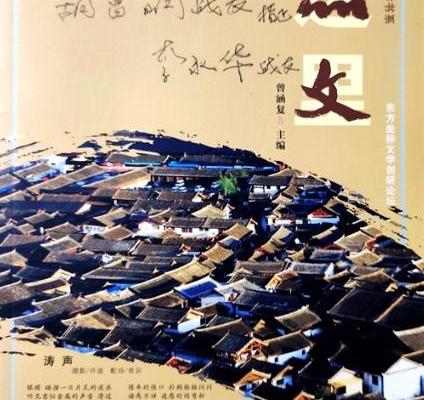我一直认为蒸汽机车是有灵魂的。
之所以这样说,也许是因为我曾是一名蒸汽机车司机,与蒸汽机车相伴了十几年。印象中,它牵引着长长的列车呼啸而来,那震撼的汽笛声、庞大的车头、喷着热气的烟筒、滚滚而来的红色巨轮和敲击钢轨时富有节律的声音常常进入我的梦里,时而缥缈如云,时而又真真切切。耳畔那“咣当咣当”铿锵有力的声音在我稍有懈怠时给我力量,给我多少年都未曾消失的鞭策。
追忆起与蒸汽机车相伴的时光,眼前总是出现一幅壮观的画面:
蒸汽机车有时像一匹骏马,动作优美,不急不缓;有时又吐着烟雾,迅疾如一只非洲草原上的猎豹。列车的轰隆声与机车的汽笛声合成一部动听的交响乐。迎着朝霞,伴着月夜,它如同一条巨龙,蜿蜒匍匐于山川旷野间……
那时的我正年轻,满怀梦想。当我驾驭着它踏上征途时,觉得钢轨有多长,梦想就有多远。
刚上车担当司炉的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位踢踏舞演员,随着列车前进或后退的节拍,踩踏着炉门踏板,迅速向炉膛内投送煤炭。炉火越旺,锅炉气压越高,列车的速度就越快。跳跃的火焰映红了我的脸庞,也映红了司机室,我便在这烈焰照映的“舞台”上挥洒着汗珠。
有时,我忙里偷闲,站在司机室门口向远处眺望。司机招呼我做好准备,列车马上就要闯坡了。我立刻行动起来,抡起铁锹,前三锹、后三锹,交叉投煤,迅速准确地把煤炭投向缺煤的火层,还不时用火钩在炉膛里左右前后翻动。炉火翻卷着、燃烧着、跳跃着,直到锅炉的气压表指针像铁钉一样牢牢地钉死在14.5千帕的红杠上。副司机不时地打开给水泵向锅炉注水,闯坡时机已到,司机马上放低手把,加大汽门,机车的声音由清脆变为低沉,像一头奔跑的雄狮,顺着两条银白色的钢轨如离弦之箭发出去。此时,我投煤的频率也在不断加快,顾不上汗流如注。随着坡度的增大,列车的速度也慢了下来,我的投煤工作更不敢懈怠,通红燃烧的煤炭在炉膛里形成簸箕形状。有时回头一看,司机仍注视着前方,手握着汽门手把,随着线路的曲直和坡度的增加,机车呼哧呼哧排着气,由一头雄狮变成了一头吁吁直喘的老牛,在机车吐出的云雾里缓缓爬行。遇到那种毛毛雨天气,机车空转不止,司机马上打开撒沙阀,向钢轨面上撒沙以增加摩擦力,这样才能制止空转。如果机车空转不断,那就可能出现坡停,机车将带着列车重新退到坡下,只能憋足劲重新闯坡。每当机车喘着粗气,好不容易爬上了坡道,我们师徒三人都顾不上擦去脸上的汗水,相互注视,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
有些区段由于坡度较大,需要双机牵引,列车由前面的本务机车统一操纵,后面的重联机车收到前面本务机车汽笛明示要增加牵引力的信号后,司炉马上把送风器打开,脚踏炉门往炉膛里添煤,副司机加强瞭望,往机车的锅炉里用给水泵不断补水,司机打开回动机手把,拉开汽门,机车立刻“砰砰砰”地吼叫起来。列车像一条巨龙,拖着长长的烟云,穿过万顷莽原,爬过座座山梁,一路上爬桥梁、钻隧道、驰草原,冲天蒸汽斜飞长空,气象万千。铁道两旁的桦树林、不知名的野花不停向后飞奔。列车风驰电掣地驶过一站又一站,惊起一群又一群的山雀,它们惊讶地望着这个长长的大家伙……
后来,我当上了司机,不知在这蒸汽机车上流过多少汗,而这幅壮美的画面永远烙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20多岁就考上了蒸汽机车司机,在从事机车乘务工作中,对蒸汽机车的每一个阀门装置、每一颗螺栓、每一组鞲鞴以及燃烧状态都有了较深的了解。当它静下来时,我站在它身边,似乎能感受到它和我心灵的相通。面对蒸汽机车,我心生敬畏,又很依恋。
再后来,我因身体原因离开了这一岗位,可每每听到它的汽笛声就觉得是它在召唤我,它那庞大的身躯总让我驻足凝望,因为它留住了我的青春,载着我的梦想。
2005年底,最后一批蒸汽机车被内燃机车所取代,我心中的感受难以言表。曾经,蒸汽机车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它所创造的昔日辉煌,我无法忘记。生命中有一段与蒸汽机车轰鸣声相伴的美好时光,并见证了蒸汽机车曾经的辉煌,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很荣幸。我坚信,蒸汽机车勇往直前的磅礴气势和迷人风采,会一直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美好记忆中。
本文图片由张伟摄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