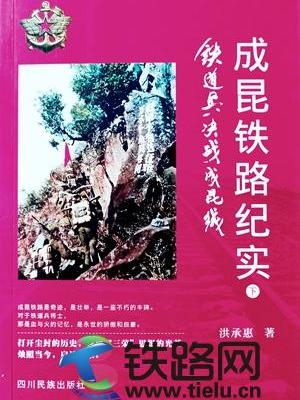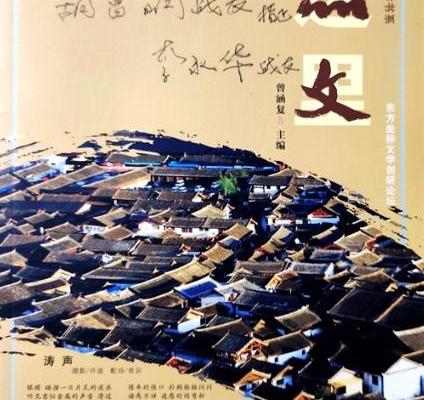舅舅曾经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和希望,如今却成了我妈和我五个姨的遗憾,更成了外婆心中不愿提及的痛。
舅舅属老七,是外公外婆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在我小姨之后盼出了一个唯一的儿子,他与大姐(我的母亲)相差12岁,作为他们那一代人,有六个姐姐的关照,可谓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别看舅舅中等身材,可是长了一张明星脸,用当时的一些人来说,那叫个“一表人才”。那时的舅舅也很是争气,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唱歌跳舞样样拔萃,一身的“文艺范”,我和小姨常去学校看他的演出。由于人品正直、性格开朗,他身边的朋友也不少。从我记事那会儿,我就一直暗下决心,长大了要成为舅舅那样的人。
记忆里抹不去的是八十年代末,那时的我也就六七岁的样子,舅舅比我大九岁,外婆家是用土胚子自己修的那种平房,后面有个小院儿,养了一只老母鸡,老母鸡每天要下一个蛋,每当寒暑假,我跟舅舅争鸡蛋吃,最后商定了,单数日归他,双数日归我,至今难忘那时跟舅舅蹲在鸡圈前等着老母鸡下蛋时的场景。
记得舅舅那会儿跑步飞快,还常常拉着我跑,年小的我常常被舅舅拽着跑很远,气儿都喘不上来,为此,每年的学校运动会,短跑项目准是我第一。舅舅还悄悄叮嘱我,不要告诉别人我拉着你跑步。
那时的舅舅爱捕鱼,常常带着我在县城的牧马河里捕鱼,有时要走上几公里远,一张网横着从河岸的两头拉通,我们就去别的地方游水,等到时机去收网,准能有大的收获。那时,每年暑假,我们常常被晒的像是涂了酱油,但是快乐是现在也能回味的,虽然我也为此挨了不少母亲的打。
后来,舅舅去了区里的城市上了高中,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是,我还是会很想念他,常常会去看他,每次他周末回来,我都会飞奔出去,双臂扑向他的怀里,每次他走时,我都很是不舍。
舅舅高中毕业后,就到了我五姨家开的当时已经有了名气的超市里工作,超市的生意很火爆,工作自然就很乏累,装货、卸货、送货,有时要忙到凌晨一两点,对于一个还不到二十岁,充满了幻想的年青人来说,现实的残酷让他短时间没有缓过神来,虽然他也任劳任怨、踏实勤奋。慢慢的,舅舅适应了这种生活,在五姨夫的帮助下,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烟酒副食店,在自己的经营努力之下,生意渐渐有了起色,顾客多了起来,舅舅也做了一段时间的“有钱人”。
99年,我在部队不小心摔断了胳膊,舅舅不远千里来看望我,还帮我请了一周的假期出去旅游了一圈。我们两穿着一模一样的西装,游遍了武汉的名胜古迹,吃遍了那里的特产小吃,花钱时舅舅眼睛眨都不眨一下,九十年代末的一万块,让我们一周花了个精光。
可我没想到,一个如此开朗、豪气、个性的人,最终输给了感情。印象中,未过门的舅妈是我在舅舅身边见过的第一个女人,她各方面都比较符合舅舅的要求。舅舅对她也很是上心,感情的付出是一方面,吃、穿、用没得说,每次她到舅舅的店里来,舅舅那个开心是发自内心的,外婆也很是喜欢。最后,不知什么原因,女方退了所有的订婚礼物,并与舅舅分了手。
那段时间,我几乎没有见过他心情如此低沉过,一个人去踢球,踢到累的爬不起来;一个人抽着闷烟,似乎找不到出口;我仿佛看见了一个男人深夜里抹眼泪的场景。全家人那时都开导他,一切都会过去,重新再来。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击将他彻底的击倒,他无心再经营,商店关了门,他无心再工作,成天的把自己关在家里抽着闷烟。全家人都尝试着关心他,开导他,帮他找工作、找对象,但似乎他的心死了,没有人能唤醒一颗死去的心,这样的状态到现在已经十几年。
进入他的房间,一个“沧桑”怎能释义,满屋的烟味儿、霉气,烟头堆积如山,垃圾屑物一片狼藉。那个英俊健硕、才华横溢的少年不知了去向,坐在阴暗角落里的那个头发凌乱、满脸胡渣、皮肤黝黑、深沉抑郁的中年人让我们每个家人看着揪心。四十出头,不惑之年,本是大展宏图的黄金年纪,他却在此堕落,我们每一个亲人都曾想破脑袋,如何能唤醒他,想到我们都快要没了希望、断了念想。
人生,只要有理想、有希望,只要身体健康,什么时候都可以振作精神、东山再起。怕的是,人生若输给那脆弱的情感,而谁失去了?谁在乎了?谁在笑?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