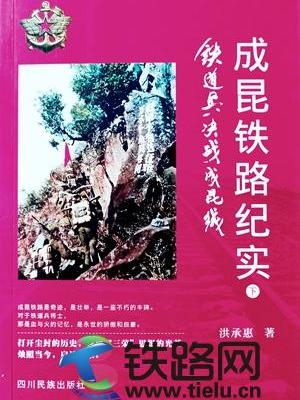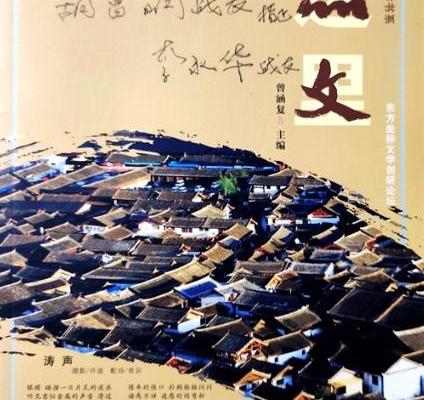已经想不起来是怎样的春季,树木照例要返青、抽芽。春风中的味道奇特,火车从远方开来,缓慢而坚定。那是一个小站,远离村镇,像一颗图钉按在四面荒野的大地上。土黄色的站舍,小候车室门前有两棵高大的雪松,上面栖着斑鸠和麻雀。它们已经习惯了火车呼啸而过的声音,人迹罕至的小站成为鸟类的庇所。小站的夜晚很漫长,野兔在雪地里留下足迹,野狗紧随其后,某种不为人所知的野物亦然。它们的世界惊心动魄,神秘而冰凉。穿过铁道线,对面是一段不算短的土丘,丘上孤零零地长着几棵刺槐和板栗。春天来了,槐花开过,雪花一样的花瓣引来一些野蜂,当然,板栗树米粒状的花蕊对野蜂有着更大诱惑。沙土地的土丘上春风荡漾,我仰躺在树下,阳光从树枝上漏下来,有时会有一只鹰在高远的天上盘旋。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我决定要“搞”些书来读。镇子里的中学旁边有家小书店,店主是个女人,据说她曾经上过高中。她长得清瘦,头发很长。她一边做着裁缝,一边卖书,书架后面是她的厨房。有天中午,我看到她在书架后面炒菜,终于明白崭新的书本怎么会散发出一股香油的味道。在她那里,我接触到了沈从文,看到了张爱玲——这些名字,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的。当然,后来也读到了路遥,读到了余华与苏童……记得,她的门上刷着蓝漆,门分两扇,上面镶了玻璃,玻璃后面拉了门帘。我推门进去,她总是低着头在缝纫机上做活。她抬起头来,冲我笑笑,并不理我,手里的活也并不停。我从书架上自己找书,坐在她对面,在“滴滴嗒嗒”的机器声中翻看她刚进的新书。那时我舍得花钱买书,书也读得太快,并不清楚自己是否读得懂。后来,渐渐明白,得到一本好书是一段不简单的机缘。例如,《德语课》是非常偶然的机会买到的,现在,我仍然会时不时地翻看。作者对命运的解读,对时代的记录,对战争的反思,都是不显山不露水的,是海底的冰山,让人着迷。
刚分配到小站时,我大概10天左右可以休一次班。休班时,我常坐火车到城里买书,中午会和朋友坐在一起吃饭、聊天,大家天南海北地聊,我常因此忘了时间,错过回小站的火车。
工作日的休息时段,我喜欢躺在床上看书,书就堆在与同事共用的桌子上。后来,我买的书越来越多,便从养路工区要了一个破木箱,用报纸将里面糊起来,用来装书。那是我最初的书箱,后来搬了几次家,书箱不知去向,书却留了下来,炒菜遗留下来的香油味道已经不在,20多年留存下来的时间的味道也已经无法描述。
这个小站后来撤销了,那两棵雪松还在,它们坚守在那里,见证了时间的流逝。我被分配到大站,那段时间,我每天清晨背着包出门,包里装着当天的饭食和一本书,一个半小时的通勤时间,我可以读60多页书,这是我每天重要的读书时间。我曾在文章《奔跑的阅读》里写道:“火车是一个容易诞生陌生感的地方,读书使这种陌生感急剧增大,同车人的面孔神秘而遥远……”那段时间,我将自己定义为“旅行者”。“他住在莫布雷火车站附近一个居室的公寓里……”南非作家库切在他的小说《青春》中将火车这种远行工具推荐给读者。火车从远处开来,然后开向远处——我不知火车站的职工们离开没有,他们是否也居住在那个叫莫布雷的火车站附近。每天早晨或者黄昏,他们夹着铝制的饭盒,穿过灰暗的街道,缩着脖子、踩着落叶走向调车常正点的火车正缓缓开进车站,一些离开的人表情沉默地站在高高的站台上,旅行箱上的标签透露出这个出走者的痕迹。这个世界似乎对于这位旅行者的踪迹并不十分感兴趣,他来了,他走了,一切都显得那么悄无声息。只有火车在制造着声音,或者说暗示着出走的意义。
回想于此,我会经常想到少年时去往另一个城市求学的经历,火车总是傍晚时分抵达那里,灰白的楼房里有零星的灯光。我永远不知道灯下坐着什么样的人,那种陌生的忧伤让年少的我难忘。那时,我无法预测到后来我会接触到什么样的人、读到什么样的书、写下什么样的文章。如今,那些灯下的人们依然生活在那里,他们没有年龄,没有面貌,没有性别,却长久地存留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在我的小说角色中活到今天,他们是永生的,像蚯蚓,断掉一截,长大一截,无绝无匮。
如今,我乘坐火车时偶尔会途经那座废弃的小站,透过车窗,我曾工作过10年的小站显得既虚幻又真实。后来,我将这段经历写进了我的长篇小说《火车站》。尽管火车站的名字是我的杜撰,人和事也多有虚构,但是,我的感情却是真挚的。我感谢在小站的经历,那段时间,我经历了蒸汽时代、内燃时代、电力时代。在我工作的20多年中,身边的人与事发生了巨变,我由乡村走进城市,我的书都长着圆圆的轮子,它们不离不弃地跟着我,安静地躺在书房里,字句安稳,酝酿深邃——等待着被我“发现”另一层内涵。随便翻开一本,在扉页上,肯定有我当年写下的题记:某年某月购于某处……有的字迹已经模糊,有的,仿佛就在昨日。
供职于济南铁路局青岛西车务段)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