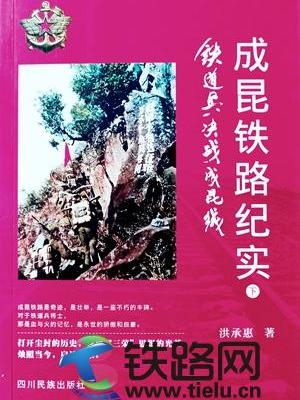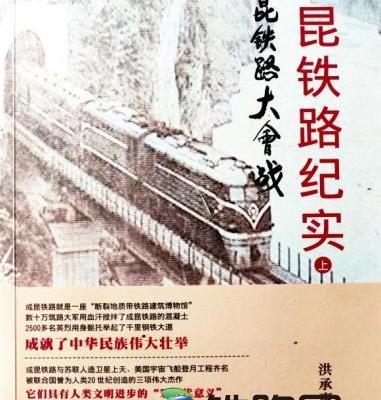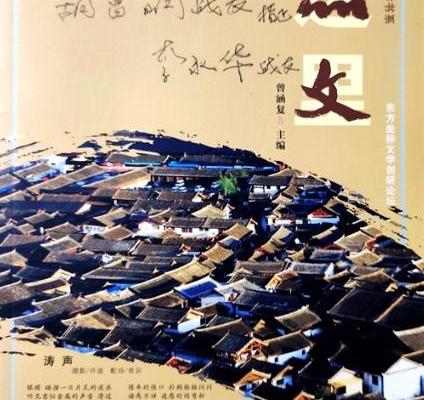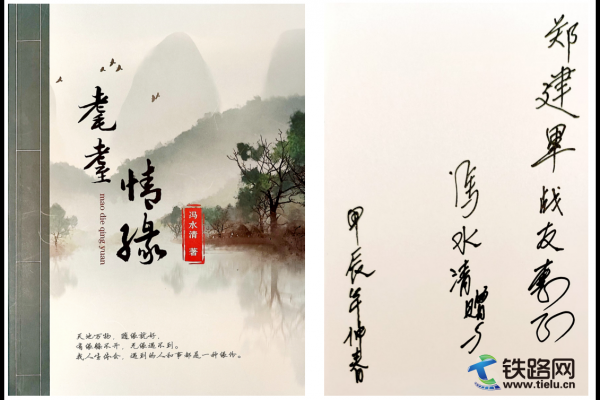签名书,顾名思义,是由作者在书内扉页上亲笔签名的赠予书。在我的案头上、书橱里摆放着不少作家文友的签名书。闲暇之时,我常信手拿来翻翻看看:一是良书益友、睹物思人;再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在回读签名书的过程中,我收获了无尽的快慰和启迪。
作为一名铁路行业内的新闻工作者、自幼喜好读书写作的文学爱好者,签名书是我珍贵的收藏品,也是我与业内同仁、文友们友情相处的见证物,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说,在每一本签名书的背后都有一段美好的记忆。上世纪70年代初,安徽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主席、著名作家陈登科来到蚌埠铁路分局考察。我受领导委派,随他一道采访。陈登科不辞劳苦,白天或找列车员谈心,或去工人家走访,与铁路职工一个锅里抹“勺子”,夜里在硬板床上写稿子,没有半点儿领导架子。他那朴实谦逊、亲切随和的形象深深刻在了铁路职工心上。陈登科和著名画家韩美林曾来到我那仅有十几平方米的寒舍做客,大家聊天时,陈登科说:“作家是属于人民的,我愿意和普通人交朋友。只有熟悉基层,理解生活,才能写出被大多数人喜欢的作品。”
陈登科将他的《赤龙与丹凤》等几本签名书赠送给我。在交谈中,我了解到他笔耕不辍,发表作品近700万字。其中,有他在文学创作初期写的百十字的小通讯、小消息,也有他的成名作《活人塘》,第一部中篇小说《杜大嫂》,长篇小说《三舍本传》(多卷本)、《风雷》(上、中、下三部)等,还有言论、随笔、电影文学剧本等。在担任安徽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主席期间,他坚持每天写作,每日创作量保持在三五千宇。多年积劳,陈登科身患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但他从未停下手中的笔,其中辛苦不在话下。每次翻看他的签名书,那种来自榜样的力量便在我心头久久翻滚,推动我不断前行。
翻开李国文的签名书《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5号》,回忆起我与这位首届茅盾文学奖和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的一段交往经历,感慨万分。30多年前,我有幸参加铁道部组织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赴前线写作组,有机会和李国文相处了近两个月。我们一同来到祖国南疆的边塞城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在与李国文朝夕相处的那段时间,我时时聆听他的教诲,他的艺术才华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李国文作为在全国早有名气的作家,和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写作在一起,没有半点儿的特殊,更没有丝毫架子。他为人随和,生活俭朴,与我们谈笑风生、潇洒自如。平日相处时,我们经常被他诙谐幽默的话语引得哈哈大笑。当时,我和李国文同住一个房间,他提议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们同住的4个人每人讲一段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这些故事我听了后便一笑了之,但李国文听后却记在心里,并把它们作为写作素材巧妙地应用在作品里。同时,李国文还经常到街头巷尾找老乡聊天。因此他的采访深入、素材鲜活,写作时可谓文思泉涌,短短一个夜晚,他就写出了1万多字的《凭祥一日》。这篇文章不仅文采飞扬,而且凭着李国文独有的眼光和敏锐的观察力,将大家“心里有而笔下无”的生动细节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李国文既具有敏锐的思想和对生活独到的观察,又拥有极具个性的艺术表现技巧。阅读他的签名书,如同进行了一次高雅文学的巡礼,能感受到作者浸透于作品的真情实感,并收获思想的熏陶与美的享受。
日月如梭,时序变更,我的签名书越积越多。其中,有我参加原铁道部召开的重点作者会议以及出席盛市创作会议时与文友交换的签名书,也有我和业内同仁一起参加全路重点事件采访时共同合写、出版的书,还有很多朋友从海外邮寄来的签名书。翻看一本本签名书,有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莫伸的《尘缘》《年华》,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朱海燕的《昨夜西风》,中国铁路作家协会秘书长李志强的《鹰背上的雪》《铿锵青藏》,《中国铁路文艺》杂志社原副主编蔡宗周的《瑞士恋歌》,铁路作家钟奋生的《红玫瑰》,铁路作家陈久全的《蓬莱大忠祠》,远在美国华盛顿的诗友张良火的《在美国见怪不怪》《张良火诗逊等,粗略算来共有100多本。这些签名书我一直珍藏在榻边与书房,书如其人,见书如见人。
一本本签名书饱含着作者的创作艰辛和收获甘甜,其间也闪烁着时代的印记和智慧的光芒。正如我收藏的签名书《我们的文学道路》中所描绘的那样,我们可以从文中“听到汽笛声,感受对铁路工作场所的亲切和热爱”以及“流动的世界在火车上的律动”。同时,签名书也让我从铁路作家们独具匠心的写作成果中捕捉到灵感的火花。这些作品打开了我观察世界的窗口,开阔了我的眼界,我总是被文字中的热忱感染。
1996年9月,我应邀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严丽霞长篇小说研讨会”。现就职于深圳大学、原在上海铁道报社任职的严丽霞,历经10年辛苦,写作并出版了13部长篇小说。在研讨会上,文学评论家雷达称她为“大陆琼瑶”。严丽霞将她的小说《都市新潮女》《冬雪银梦》签名并赠予我的同时,对我讲了她的一次经历。一次,严丽霞去靖安采风,当地负责接待她的同志一听说她是严丽霞,马上说:“我早知道你,能不能送我两本你的签名书?” 严丽霞手边没有书,便与这位同志一起去当地新华书店买。书店经理对她说:“你的书很畅销,一来就卖完了。”书店里的书脱销了,严丽霞一行到附近的租书摊去找,结果只找到一本《爱里乾坤》。这本书封面没了,书也破旧不堪,书摊主说:“借这本书的读者很多,便成了这个样。”严丽霞听了心头一热,把这本“破书”买了回去,并珍藏起来。她说:“希望我的作品不但给人们带去阅读的享受,而且能带去心灵的净化。”严丽霞的这番话对我有巨大的激励作用,成为我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一面镜子,让我时刻反思自己。
回读签名书是一种快乐,更是一种享受,是签名书激励我的文学创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多年来,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坚持文学创作,至今有500余篇散文、诗歌、杂文、报告文学作品在《人民日报》《文汇报》《中国文学》等报纸杂志上发表,诗集《亮了出发的信号》由安徽出版社出版。
每次翻看珍藏的签名书,我都为业内同仁和文友们的成功感到自豪。同时,愿这些置于案头的“珍宝”能激励我保持创作的热情:生命不息,创作不止。
退休前供职于上海铁道报社)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