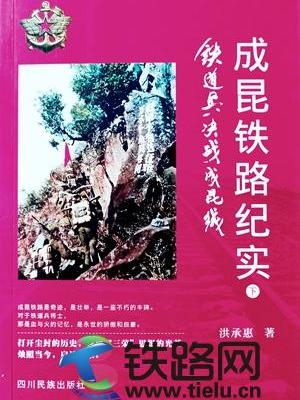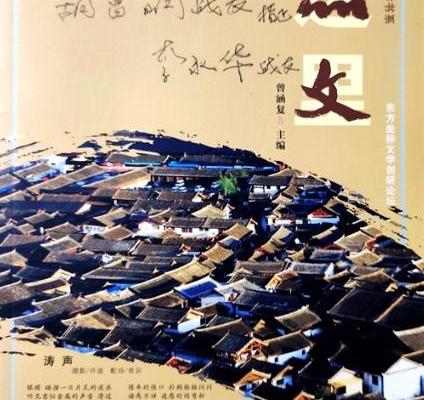■左马右各
记得早年读铁凝的一本散文集,该是很早的事情了,她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一句话“散文河里没规矩”,当时读到就眼前一亮。这么多年过去,这句话也一直铭记在心。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作家不应该被某种事物既有的窠臼拖累和限囿。他要勇于打破和建立。其实这句话,还可推而广之,在所有关涉文学写作的领域内占据某个高点,张扬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所具有的某种野肆品质和孤世雄心。它的真正内核是张目作家的创生力,让作家的写作实践不断在自否与突破中,实现踏入某种写作臻境的自我涅槃。
近日读著名作家杨晓升的中篇小说新作《病房》(小说原载云南“大益文学”书系第二辑《城》,漓江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就深刻感到这样一种内生于作家灵魂深处并不断腾升的创生原力,激荡在小说文本之内。小说以京城某家三甲医院的4号病房为文本切口,经由退休教师李建文中风入院这一引线,接续推出王美丽(护工,曾是李建文的学生)、唐慧娟(护士长,曾是李建文的学生)、2号病床刘平民一家、3号病床某县组织部长雷政富等一干人物,把一个反映医患生态、具有批判意味的故事,通过精彩的叙事架构和人物浮雕式的凸显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让人在阅读后,对作家拆解在一根人性链条上的纷繁世界的能力心生感佩。而这根人性链条,隐身在小说的叙事链条之后,就像镜子的反面,折射出沿着生活的某个剖面断崖式切开的人生场景。不过小说文本采取的叙述方式是从一个更为广阔的叙事空间回退、收缩,以一间病室为基点,完成其向现实世界的逐渐扩张、辐射。
人是有原欲的生物,而这种原欲又恰是人性的根源所在。引用在本文的原欲是个广义概念,但我在使用它时,又只把它限定在两个域界内——善与恶。而这善与恶又是受限于一个狭义的解释义,也就是它只涉及人在日常和普泛意义上的小善、小恶行为之内。我不想让这样一对概念在披沥它既有的本空歧义后又失陷于故为造作之空的二次沦陷中。而人世的芜杂早已把这样一对互生概念折弄得面目全非。也就是如此古老、几乎是乏味的一个命题,在对人间世界进行着不断的撕碎和颠覆,又让其在几近绝望之际勉力给出人性微光一般的修正和救赎。它对应到《病房》这个小说文本的人物身上,就是李建文古板、严苛的教学风格,为人师表的精神自省,以及深受传统影响潜存于内的仁心善举。他为当年由于严责王美丽而导致其失学一事,一直耿介在心,不能释怀;遇到刘平民一家受困医药费的负担而陷入挣扎的绝境时,拿出自己的治病钱给予解危。这样一个人物,看着像似具有了某种善爱化身的影迹,但他又是一个迂腐的教书匠,在人生遭际中也向权力、分数、升学率、荣誉这种无形的既存桎梏妥协,甚至避让。即便是在病床上,他能置病躯于不顾,敢于替刘平民一家伸张正义;但当他的学生护士长唐慧娟做出媚官私己的举动时,他亦采取了和稀泥和明哲保身的暧昧态度。在这个人物身上,既有人性光芒的磊落,也不乏人性失色的黯然时分。我觉得作家在面对这个人物时,内心也是矛盾的。因为他深知人性的复杂与乖舛。这一矛盾性在李建文因尿急而失态——不只是失态,简直是尊严丧失殆尽,这一生理窘困的描述上发挥到了极致。小说阅读进行到此,我不禁感到脊背一阵寒凉。作家要忍住多么砺心的内痛,才能下此“毒手”,让一个曾是教师、现为病人的老人落魄如此,又如此不堪。也正是这一细节的横出,让李建文这个人物在小说文本中获得了他最具人性姿态的丰满,而这个姿势——它是一个能站住的人的姿势,也是作家探微人性的精敏把握。
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王美丽,让人感知起来,要远比文本呈现的既有形象困难得多。初读这篇小说,一遍下来,恍惚觉得作为一个主要人物,王美丽的形象塑造似是单薄了些。但经过细读,特别是个别章节的反复重读,便推翻了之前的判断。她更像是一个数值的复数。在她貌似平淡的人生经历中,却隐含个体生命的诸多复杂性。
李建文和王美丽作为20年前的一对师生,在医院意外相遇——按照常理推之,那将是一个亲切场景,“叙旧的话恐怕得一箩筐”。但王美丽却在内心恨着李建文,恨这个当年葬送自己在花季年华求学前程的班主任老师。在王美丽偏执的认知中,就是他毁了她的人生。作家对这个人物的人性挖掘颇费心机:让她以一个负责任、深得病患家属信任的形象出场,但当师生巧遇发生,又迅速急转,让她变身成为一个自私的复仇者,并在开始履行护理职责的当天,就一再折磨已是病体缠身的李建文,让他窘迫,出糗事,丧尽尊严。但作为普通人,她内收的善心、一个护工的基本职责又在时刻唤醒着她,让她那获得报复快感的内心重向人性本位回归。毕竟,她也是一个身份卑微、正在经历家庭变故的人,是在生活中受尽苦难的人。从这个层面上讲,王美丽也是一个病人,只不过她的病灶隐藏在不曾裸露的内心世界里,但她又是一个人性自愈机制尚未完全失控的病人。她虽无宗教信仰,但内心有着像生养她的故土那般醇厚的不泯善愿,这已足够让她在滑向罪的渊薮时实现自我救赎。在这一点上,3号病床的患者、某县组织部长雷政富以及他那飞扬跋扈的老婆,狗眼看人低的随行护工,却处在永远不得救赎的深渊里。
杨晓升的写作一贯保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洞察和犀利尖锐的批判姿态。
应该说王美丽这个人物真正丰满起来,是在她发现2号床的病人刘平民的女儿刘彩霞为了使父亲得到更好的医治,不惜卖血筹款准备给主治医师送红包这一秘密之后。从她劝阻、制止刘彩霞继续卖血到勇敢地挺身而出,拦住高院长及市纠风办检查组一行人员,由起初的诘问到陈述刘平民一家的苦堪境遇,在根本上使这个身陷医贫陷阱的家庭再次获得挣扎出来的希望。可以说,至此王美丽这个人物已经获得擢升,似已具有某种人性光芒的意味。但更为可贵的是,她只是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应该做也做成了的事。当医院借此大肆宣传某种表象正义并忽略掉她这个事发者的时候,她并没感到失落,反而生出一种莫名的心安,仍“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护工工作”,也不失美好地为刘平民一家的境遇改变祈愿。这才是她人性深处最为光辉的地方,却藏在灵魂深处。作家挖掘到了它——并使之占到一个隐存的人性高点上。
这时,再回观这个人物,就会发现她起初用马桶水为老师涮水杯、一而再地把雷政富的牙刷戳到马桶内解恨,就具有某种典型的象征意味。她的这些看似是纯粹出于个人原因的泄愤行为,却有着为一个在人生底层挣扎的生存群体寻求某种宣泄通道的“代言人”意味,但这无疑又是一个社会人夹杂着愚昧的行为。这种双面人格,也使得王美丽这个人物形象变得真实可信。
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杨晓升是一个愿意在写作中不断制造痛点的作家。如在这篇小说中他对“医院开恩”和“遇到贵人”等句式的使用,以及刘平民一家那种小人物的感恩方式——一再对施恩者下跪、不断恩谢,都让我在阅读过程中感到内心充满针芒锐刺的痛感。
在这篇小说中,还有一个人物引起我的多重思考。我一直试图僭越内心某种看似合理又适恰的观念、定位,来近距离打量这个人物。她就是唐慧娟。我的阅知是,在这篇小说中她是一个不无悲情的边缘人物。当唐慧娟这个人物遭遇到小说结尾的命运时,我只能对她报以深切的同情,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对她说点什么。她无疑是对这个社会和她所经由的人生有过清醒认知的人,但我想说,或许正是这份过度清醒,让她失去了本应让内心葆有的某种珍贵品质。
在这篇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小说中,却有着一个类似轻喜剧般的滑稽人物出场,他就是3号病床的患者雷政富。我是说这个人物名字。作家虽把这个人物置于人性挞伐的彼端,但又让其不失人的丑恶形迹。初见这个名字时,我霎时一愣,以为自己搞错了,它怎么这般熟悉,又在瞬间忽地想了起来,便不由得会心一笑。作家为一个小说人物起这样的名字,是出于戏谑,还是想隐含某种机锋,或是有所喻指?这不得而知,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所具有的符号意义是明显的。
著名评论家谢有顺在一篇小说讲稿中这样说道:“小说的写作,有时不应是扩张性的,反而应是一种退守,退到一个自己有兴趣的地方,慢慢经营、研究、深入,从小处开出一个丰富的世界来。”
在杨晓升的小说写作中我看到了这样的异变景象。从他近年发表的小说《介入》《身不由己》《日出日落》《天尽头》《风过无痕》《疤》等一系列作品中,我们已看到完成转身的作家影像。他看似是在回退,但却以新的写作实践经营着一个“从小处开出一个丰富的世界来”的创作愿景。在一次和读者的见面会上,杨晓升说:“如何在作品中摆放现实是对成熟作家的一种艰难考验,这既考验作家处理现实的能力,又考验作家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对生活的认知。”
《病房》这篇小说为作家的言说做了最好的诠释。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