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就这样带我们去远方
■姜浩峰
与陈建华教授约在威海路上海报业集团大厦底楼咖啡吧喝东西,馆子名曰“申活馆”,主办方是《申江服务导报》社。这份报纸那醒目的“申”字,是20世纪早中期著名的《申报》的报头字。
那个年月,有些上海人一度将所有的报纸称作“申报纸”,可见《申报》之红火。
那个年月,火车出行也彻底改变着国人的世界观,改变着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作为上海交通大学的讲席教授,陈建华先生不仅研究元明清文学、近现代通俗文学与报刊文化、中国文学与视觉现代性、中国早期电影,还将研究的触角伸向了交通运输领域——民国时期的火车。
那些看似光怪陆离的文学作品,因为发生在那一时期的火车上,而显得颇有文学意义上的指向性。那些与火车有关的电影,则带人更直观地进入了那个年月。
铁路乘西风而速东渐
铁路、火车,诞生于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及至西风东渐而到中国。在陈建华看来,当火车甫一出现的时候,无论在英伦还是在中国,所遇到的人情事态颇有相似之处。
“火车进入中国,有人反对,有人赞成。我觉得还是赞成者占多数。”陈建华说,“19世纪,中国人中最先对火车有体验的,还是出洋访问的官员,比如郭嵩焘,或者像王韬这样的文人。当中国人出洋后,发现西方要比我们先进得多,他们把火车、铁路、桥梁等视为一种具有结构性的意象。其中,火车特别具有象征性。对于火车,他们持有积极的态度,继而把火车跟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认为西方的制度比当时中国的制度来得先进。所以说,当时的火车,作为意象,带有人们对西方的渴望。”
在《文以载车:民国火车小传》里,介绍了192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一套八册《国外游记汇刊》,其封面上中框是书名,四周画有各种交通工具,有城市马路、跑着的公共汽车、有轨电车、双轮马车、自行车和独轮车;有天空、飞船、飞机和轮船,其底部是一列通栏的长长的火车,从隧道驶出。在陈建华看来,这一幅交通图,呆板而有趣。早前中国人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国门撞破,心扉炸裂,然而之后,中国人学会了驾驭,学会了奔驰游弋在新的时空和文明之流里。
当然,在清末的铁路实践中,亦有类似吴淞铁路这样因利权问题而遭遇拆毁者。在陈建华看来,这主要还是为了争夺政治和商业利益。从铁路本身的开通来看,民众当时还是开心的。《文以载车:民国火车小传》中,写到一条通往嘉兴的铁路,是中国人自建的,举国上下对这条铁路都持欢迎的态度。
“火车在中国出现后,反对者当然也有。火车为普通百姓带来的不一定全都是好处。”陈建华说。在书中,他亦如此感慨:交通工具凝聚着资本的力量,驮载着象征的、政治的、教育的、文化的资本。没有交换和流通,思想长不出翅膀,历史成不了火车头。
当火车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的生活习惯、时空想象都开始改变。时代,不同了……
文学因钢轨而更悠长
《文以载车:民国火车小传》之所以能够成书并于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之际付梓,是因为陈建华写了几篇与火车有关的随笔,连载在《上海文化》杂志上。
“我对现代文学里的交通工具有兴趣,缘起于几年前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上过一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衣食住行的课。”陈建华在书的自序中如此写道,“其中关于‘行’的部分就会讲到鲁迅的《一件小事》、老舍的《骆驼祥子》、张爱玲的《封锁》、周瘦鹃的《火车上》、藤固的《摩托车的鬼》、萧红的《蹲在洋车上》等,仿佛读得之秘而不免喜形于色的样子了。”
作为便捷的交通工具,火车出现在许多文艺作品里。在陈建华的书中有一篇《清末文学海陆空》,讲到清末《绣像小说》刊载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以及1908年《月月小说》刊载的包天笑的《空中战争未来记》。这些小说颇有点儿科幻的味道。而当陈建华讲到当时文学作品里陆地上的交通工具,用了“就很惨”三个字来形容。从清末到民国,铁路带来的民族记忆一直没有消失,直到1926年6月《太平洋画报》中,竟然还在刊载一幅内容为国际专列的漫画,题为《中国领土内之怪物》。在北伐战争的声浪中,屈辱的记忆再度浮现。陈建华对于清末民初的文学有着独到的认识与见解。这些认识,在他的《帝制末与世纪末──中国文学文化考论》《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等专著里有深入的阐述。单就火车与文学的关系,陈建华对我说:“火车被当作一种具有指向未来意义的意象,成为‘速度’‘光明前景’等的象征。”
陈建华在《旅行比喻目的》一节中,选择了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选入的3篇作品——孙俍工的《前途》、冯沅君的《旅行》和王统照的《车中》。在他看来,20世纪20年代初,正是新文学运动的“特快列车”加速前进之时,车头两边挂着“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旗帜、朝着富强中国的理想目标突飞猛进之际。在孙俍工这篇基本没什么故事情节的小说中,火车充当了主人公的定位。无论出发前,或者在途中,不时可以听到一种主旋律。当有人不耐烦时,就有人说:“我们要晓得一到目的地便快活了。无论如何难受只得忍耐,忍耐地等着1中途上车者会说:“好了!只要到了站就不怕了!一会儿工夫便可到,到了就好了1陈建华认为,这些话在重复一种集体意志,对火车满怀信赖,搭上火车便意味着幸运,一到目的地便好似到达幸福的彼岸。
陈建华还特别提到陈蝶仙的小说《新酒痕》。小说里,赵氏父子乘的沪杭特快列车。老子要乘三等车,拗不过儿子才忍痛坐了二等车。儿子一席白纱长衫,外罩缎纱对襟马褂,头戴软胎草帽,看着风流倜傥。而老子却手里拎着个马桶。原因是不舍得扔。小说里,这只马桶初起时放在座位下,被人嫌弃臭而放到盥洗室,又被人撒了泡尿在里面。老先生拎着马桶下了车,在车站马桶跌落溅了一身尿。在陈建华看来,那个年代,一些中国人的家庭重心移向经济和体面,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暗藏着种种象征,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也不那么善恶分明了。总之,文学因钢轨而更悠长。
电影因火车而富隐喻
在陈建华看来,火车与电影亦有各种有趣的组合,譬如“左拉的《野兽与人》写火车、车站上发生的罪行。其实,这些并不是火车才独有的问题,左拉的小说本身讲的是社会问题。这部小说拍成了电影”。
还譬如好莱坞电影《上海快车》,这部约瑟夫·冯·斯坦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执导的影片,由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克里夫·布洛克(Clive Brook)、黄柳霜等演出。《上海快车》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列行驶在中国大地的火车上,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这部影片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提名。最近,美国亦出品了一部火车电影《火车上的女孩》。
在陈建华看来,中国有关铁路、火车的电影,有的也有隐喻。而如今高铁已经普及,旅途变得与过去不同了。至于高铁上发生的故事,以及以高铁为背景的电影,还有待未来人们的创作。
本文图片由陈建华提供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
铁路资讯
- 农历小年车票开售 铁路春运售票超1亿张08:09
- 这一年,你的平安有铁路人在守护08:09
- 京张“四电”通过初验08:08
- 铁路新装备拉动“公转铁”08:07
- 推进安全生产整治有新招08: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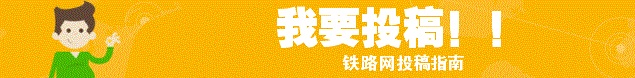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