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铅字
读书的动力,大抵与机缘和兴趣有关。铅字与墨香,引导我做工、读书,有如熟悉的钢轨,铺展得再远,也要念及起始的地方。因自醒慨叹而写诗,经岁月沉淀而出书,往昔与当下,皆应珍惜,有如脚下的黑土地,带着彼时绿皮火车的风笛阵阵,追赶着此时高铁闪过的一瞥。
1989年5月,我初到齐齐哈尔铁路印刷厂实习,一进铅印车间,浓厚的油墨气味扑来,十多台机器在运转。刚开始,我还感到新鲜,待久了,耳朵里就只有“呱嗒呱嗒”的声响。收集印张的竹条像张开的五指,扇来扇去,两个工友负责一台机器,一人上墨、码纸、备料、看机器,一人在机台上干活,机台上的工友在手工续纸,左手带纸,一张张地移向轮滚的方向,右手指尖划纸、指肚轻扫、及时补纸,熟练又专注。踏进印刷厂,我晓得了,在这里,书籍是不折不扣的产品,续纸不到位、油墨加晚了都可能出废品。印刷工辛苦,机器坏了,若是小毛病,要爬下去自己修,干净的工作服,常蹭得一身黑。
一个月后,我被调至装订车间。车间在临街的平房内,没窗户,全是木头架子做的工作案。当年的装订多是手工作业,折页子、刷胶、码车。装订车间有30多人,只有关师傅和纪哥两个男人,把持着成书前的最后一关——裁切。他们干活干脆,用了不少年的裁纸刀还在工作,一刀下去,咔嚓一声,毛纸边落下,三面裁完,一摞清亮的新书便摆在眼前。环顾厂房之内,凡是目之所及的书,我都会翻一翻,看一看。看上眼的,就在午休时,把裁书的副品纸毛子,归拢到墙边,构筑成厚厚软软的床榻,躺在上面,随手拿一本书读,不知愁滋味。那些刚装订成册的书,还没发到书店去售卖,我就先看了。
在装订车间工作,看到师傅们做精装书,我就想到了我的旧版书《杜诗详注》,那是我用助学金在齐齐哈尔解放门旧书摊淘来的。我这套《杜诗详注》有些破,也不是什么珍本,我便央求做活精湛的师傅帮忙重新装订一下,也弄个精装本。不精装则可,一弄就觉得对不起人家,真是费手工、费心血。先是设计封壳、书芯的脊背、书角造型。因是私活,要找美观适用的剩料,还要与车间主任打招呼。先是加工书芯,锁线、压平、书背刷胶,然后扒圆、起脊定型、压实书背,书芯背上粘纱布、粘堵头布,粘书背纸,最后制作书封壳,一套精装书呈现眼前。至今,我看着这套《杜诗详注》,还是感念师傅们的辛劳,此书陪伴我有30年了。杜诗注定流传千古,我装修了他的“门面”,可能淡忘了他的内在,尽管如此,在普洱与书混杂的书柜里,瞥上一眼,似老友,闲坐无语,也暖心。
再过两月,我又去了拣排车间,顾名思义为拣字排版。当时的拣排车间,一人高的“字丁墙”围成的隔断,架子上有数不清的小格,每个小格子里都摆放着很多“字侗,不同字号大大小小陈列其中,常用的是五号字,放眼一看,眼花缭乱。刚到,我们就被要求熟悉字格。事实上,只有把排列顺序记熟,甚至闭眼都能知道哪个字放在哪个格子里,才能提高速度有效率,不然拣起字来,迷茫半天才找到一个字,师傅们已经拣了几十个了。
拣字的多是女将,说是师傅,有的比我们也大不了几岁,她们一手拿稿和字丁盒,一手拣字装版,眼疾手快,脑子还开不得半点小差,一个小时可以拣好几千个字。拣字辛苦,常年拿捏砥磨铅字,很多人的手指都磨出茧子,有的甚至微微变形。车间过道是补装铅字的字盒墙,中间摆着两台敦实的打版机,大家把拼好的铅版放在台面,着墨、摇轱辘,就弄出了装版大样。
拣排车间紧邻调度室,调度室往来多墨客,再加上校对、看稿样,便见到了一些编辑和作者,也能在第一时间看到稿子。其间,我印象最深的书叫《鹤魂》,汇集了徐秀娟生前创作的诗歌、日记和一些回忆文章等。我读着《鹤魂》里她的遗作,从朴实的文笔、真挚的情感中,了解了她短暂而荣光的一生。徐秀娟在齐齐哈尔扎龙自然保护区,从小伴着丹顶鹤长大,十几岁学着养鹤,考入东北林业大学动物系,因家境不好,求学之路十分艰难。毕业后,她被邀请到江苏盐城,指导鸟类保护工作,并组织建立了丹顶鹤冬季饲养常1987年9月16日,她为了寻找一只飞失的丹顶鹤,不幸沉入河底,以身殉职,年仅22岁。在与《鹤魂》编写者交谈后,我对她留下的文字更加尊敬,不仅是因为她的不幸离世,而且感叹于她朴素的语言,如顺流而来的竹排,看似平常,实则力道非常,令人为之泣下,令人奋进向上。
行走的铅字,是我精进的动力。工余的时候,我想写写与工作有关的东西,拼版拼久了,习惯了单调的劳作,走神的时候,我仿佛看见桌案上的铅字,一个一个动了起来,有如训练有素的兵叮他们穿着一袭银色的铠甲,周身透着寒气,在桌面上列队而行。顿时,我觉得不算宽的工作台变得虎虎有生气。做拣排工的我,竟也可以拥兵上万,也可以有一次运筹帷幄,这些铅字兵丁身后泛亮的背景,如浩渺的大江,是我无论怎么读也读不完的书籍和不可知的未来。而与我工作案对峙的那侧,那些拣字的师傅用纤柔的手指,让成千上万个素盔素甲的铅字,在铁盘上组成了书的方阵。铅字,多像我们的苦乐年华,于是我写下了《铅字铅字》一诗。
写得多了,也陆续获了些奖,这让我感到写作与劳动贴得近些,似乎更适合我。在王新弟老师的帮助下,我的第一本诗集《怅然的笛音》在1993年由华艺出版社出版,新弟老师以《执锄于岁月的田垄》一文为我写序,那一年,我22岁。光阴虚掷,25年后,我的第二本诗集《火车奔向雪国》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发行。
我的诗歌内容多是围绕着铁路转,从齐齐哈尔到哈尔滨的工作变动,从感怀铅字的神秘排列,到中东铁路浓厚气氛的浸染,让我集中精力写了些有关地域铁路的诗歌。尤其读了铁路史和近代史方面的书籍后,我就更加感到我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是个有故事的地方。站在我家楼下,哈尔滨东大直街与龙江街街口,左侧有两座随着中东铁路而来的东正教堂,再远些是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巴夺烟厂,右侧是老秋林公司、原各国领事馆、圣尼古拉大教堂遗址。
站在我办公室的窗前,能眺望到百年霁虹桥,桥下火车轰鸣而过,桥上浮生自忙,因高铁扩展的场站,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我觉得站在传统与现代的路口,先进的印刷术与胶滚着油墨的铅字并不矛盾。
凡事皆可溯源,读书与写作亦然。
供职于哈尔滨铁路物流有限公司)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
铁路资讯
- 农历小年车票开售 铁路春运售票超1亿张08:09
- 这一年,你的平安有铁路人在守护08:09
- 京张“四电”通过初验08:08
- 铁路新装备拉动“公转铁”08:07
- 推进安全生产整治有新招08: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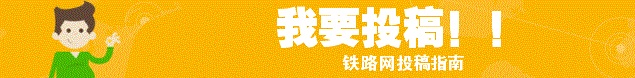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立场。